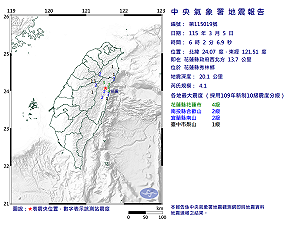第一次見到翁啟惠前院長,不自覺地激動,眼淚在眼眶中打轉,他卻很淡定。為何激動 ? 有個這麼冤屈的名人,無論如何吶喊,頭像被布袋蓋住了一樣,喉嚨也被掐住了,聲音怎樣都出不去。
去年七月中一個午後,不認識的兩個陌生人,在中研院的卸任院長辦公室喝起了第一口茶。「我不認識你,也不知道浩鼎案是什麼,我的第六感告訴我,你的冤屈沒有人懂,我專作白話文翻譯, 讓我來幫你吧」。
從那一天開始,浩鼎案的案情開始有人聽得懂了。
跟一位剛認識的友人無意間的對話,才知道他跟翁啟惠先生是深交好友,我三催四請,等了三個月,終於見上一面。 翁前院長應該像驚弓之鳥,一聽說我早年有新聞記者的背景,考慮了三個月,終於肯見我一面。對於媒體的驚恐,走過那一段腥風血雨的日子, 我完全理解為何他這麼害怕見到我。
浩鼎案是什麼 ? 是台灣社會主流思潮裡面最討厭的那一塊,富人玩的金錢數字遊戲,股票翻動兩下就勝過許多人多年辛苦所得。在網路世代崛起後,被剝奪感、不足感、貧富差距大的失落感,種種情緒加總起來,剛好在政權準備交替的時候,又被抹上政治顏色,所有的負面因素加起來,成就了一個浩鼎案。 翁啟惠在這樣的環境因素下,大眾享受的名人屠宰樂,就這樣被生吞活剝了。
也許大家忘了,翁啟惠只是個待在實驗室的科學家,他身上沒有揹著算盤或計算機。他不是商人,卻揹上商人的原罪,整個社會氛圍繞著仇富情緒走,他的冤很大一部份源自於此。
第一次見面完,他送我走到電梯口,在電梯門關上那一刻,我看到一位身軀單薄瘦弱,身心被摧殘到氣若游絲的科學家,不該走的這趟官司路,將近三年時間的折磨,已經讓人形銷骨毀。這位曾經管了5000多名博士,9000多名員工的中研院大院長,面容不時掛著謙虛客氣,說話慢條斯理,讓旁人好生心疼 。
家父母都是癌病患,癌病家屬的痛我最能感受。我當時只有一個心念,儘快把院長送回實驗室。失去父親的痛,是我人生中的最大殘缺 。有多少個家庭還在忍受這些疼痛,翁院長的寶貴時間應該是用來救苦救難,為癌病家屬解痛,不是花時間走在士林地院這些台階上,來來回回幾十趟,時間一點一滴的消逝,讓傷心的人更傷心。
院長要得救,最重要的一件事一定要解決。台灣社會聽不懂浩鼎案,沒有人有辦法用白話文解釋這個案情 。 法院不能,律師不能,媒體不能,翁院長更不能。我用文字解釋了這場生技大浩劫,及這位生技教父在這場大浩劫中承受多大的冤屈。
翁啟惠在2014年拿到以色列沃爾夫獎,這是僅次於諾貝爾獎的化學獎,2016年三月美國威爾許獎,2016年英國皇家科學獎,時值浩鼎案爆發,翁啟恵兩個獎全部放棄。
如果拿了沃爾夫獎和威爾許獎兩個獎,照國際慣例,下一步就是諾貝爾獎。 2016年預測的諾貝爾獎就是翁院長的醣分子研究將獲得。
與諾貝爾獎擦身而過,他如在煉獄般過生活二三年。我的了解,只要檢察官放棄上訴,官司終止,美國的威爾許獎將再重頒給翁院長。意思是,台灣近日真的可能拿到一座諾貝爾獎,決定權在台灣的檢察官手上 。
既是不該走的官司路,烏龍一大場,檢察官是否有放棄上訴的勇氣 ? 以蒼生為念,以翁啟惠為人類社會偉大貢獻為念,請讓翁院長回到實驗室,為眾生解苦解憂,繼續他的癌症疫苗研究吧!
那天午後,卸任院長辦公室裡來了一位陌生人 ,一個容易情緒激動的文字工作者,一份感動讓我走到今天。台灣人如果跟我一樣感動,讓我們一起給翁啟惠先生力量,好嗎?
王雅君 (文史工作者,後成為翁啟惠親友團成員 )
發布 2018.12.30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