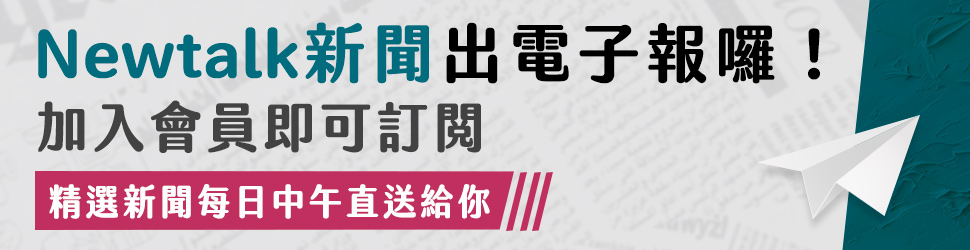二零一二年出走中國前夕,中共當局不准我與「天安門母親」發起人丁子霖、蔣培坤夫婦話別,多名國保警察押送我們一家三口一直到飛機的登機口。
我不知道什麽時候才能再見到丁老師和蔣老師。不過,我請朋友將蔣老師幾年前送給我的一張鐫刻着胡適名言「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木板郵寄到美國。
蔣老師是一位美學家,八十年代中期,在劉曉波的博士論文答辯會上,他是評委之一。蔣老師心靈手巧,書法、篆刻、木雕,樣樣拿手。他在鄉下尋覓到一塊經歷了滄桑歲月的門板,鋸成四十公分見方,將我最喜愛的胡適的這句話鐫刻其上,作為給我的生日禮物。
如今,我把這張蔣老師親手製作的木板挂在書房,寫作累了,抬頭看看,便能從中汲取無限的力量。丁老師是丁文江的姪女,丁文江是胡適的密友。從胡適、丁文江到丁子霖、蔣培坤,再到劉曉波和我,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的抗爭與悲情,九曲迴腸、歷歷在目。
印章與洋酒背後的故事
位於台北郊區南港的胡適紀念館,分為三個部分:一爲胡適當年的住宅,現辟為故居。二爲陳列室,爲美國友人史代於一九六四年捐贈建造。這兩部分都在中央研究 院院內。三爲胡適公園和墓園,則在中研院大門之外。胡適的墓園建在小小的山崗之上,居高臨下,可以遙望草木枯榮、雲卷雲舒。
紀念館的館長、歷史學者潘光哲博士,是我多年前就認識的老友。胡適是其一輩子研究的對象,由他親自來導覽,自然是如數家珍,很多看似尋常的展品和陳設,一 經敷衍,頓成精彩故事。
在展出的胡適的日用品中,有幾套現在看上去仍然嶄新的西裝革履,有各種證書,還有幾方印章。潘光哲提醒我留意其中一方看似尋常的印章,旁邊之落款爲「學生 胡頌平贈,臺靜農刻,一九六一年於台北」。
作為五四那代學生的臺靜農,在白色恐怖的高壓下,後半生只能縱情詩酒,醉心書法和篆刻,心境之幽微與作為老師的胡適十分近似。
胡頌平和臺靜農這兩名胡適的學生,一名出自中國公學,一名出自北大。而這兩所學校正是胡適一生中服務時間最久的地方,胡適對這兩所學校的畢業生始終很「偏心」,能照顧就盡量照顧。
北大自然不必説了,走到哪裡,胡適都能聚集起一群「北大派」。而胡適擔任過校長的中國公學,是上海的一所私立學校,不少國民黨達官貴人都畢業於這所學校。胡適在任上力抗國民黨推行的党化教育和奴化教育。也許害怕這所學校的自由主義特質,國民政府遷台之後,中國公學未能順利復校。
在胡適故居客廳的茶几上,擺放着胡適生前飲用了一半的白蘭地酒。胡適並不嗜酒,偶爾喝幾口,也是飲少輒醉。他隨身帶上一小瓶酒,是提防心臟病發作的「救命藥」。
然而,偏偏在那場爲學生吳大猷舉行的慶功會上,胡適忘了帶上這瓶酒。據潘光哲説,館方將這瓶酒留在原處,是要「引誘」老先生哪天晚上回來,可以偷偷地喝上兩口。
胡適心臟病的第一次發作,是在駐美大使的任上,那時他只有四十七歲。從此以後,這個危險的疾病就如影隨形。那時,胡適馬不停蹄地展開民間外交,直接訴諸美國民眾,到各大學和民間社團演講,獲得了三十三個名譽博士。然而,由於爭取美國援助未能成功,胡適受到蔣介石的猜忌而去職。
一個愛熱鬧的孤獨者
在台灣,很多名流的故居都是日治時代的日式老宅,胡適的居所則是少有的美式平房及院落,是蔣介石撥出專款爲胡適修建的「院長官邸」。 胡適是個愛熱鬧的人,訪客絡繹不絕,談笑者固然大都爲博學鴻儒,往來之人中亦有若干「白丁」階層。胡適夫人江女士喜歡打麻將,胡適偶爾也陪着打上幾圈,這也符合胡適所説的「一等人怕老婆」的原則。
不久,有風言風語説,中研院院長的官邸中傳來麻將聲,有辱斯文。為了避嫌,胡適在台北另購一處住宅,讓夫人可以無拘無束地在那裡打麻將。於是,這座郊區的 「院長官邸」,夫人很少在此居住。在白天,還有秘書和工友隨侍左右;到了晚上,就只剩下胡適一人獨居了。
有一年,颱風來臨,屋頂漏雨,胡適親自動手搶救藏書,忙了一整夜。第二天,請工友來修屋頂。多年後,那位工友回憶說,當他從梯子上走下來時,發現院長笑吟吟地端來一盤包子慰勞他。
胡適的書房並不大,且採光很差。向陽的一面牆,設計頗有問題,牆上只有幾排小小的方孔透光,讓人有坐牢般的感覺。若是按照熱愛光明的殷海光的意思,必定要把整面牆都改成亮堂的落地窗戶才罷休。隨和的胡適沒有提出修改意見,隨遇而安地在這間並不舒服的書房裡讀書和寫作。
作為中研院院長,胡適的應酬和公務頗多,仍忙裡偷閑、手不釋卷。在書架上,可以看到諸多胡適精讀過並加以批註的書籍,如魏特夫之《東方專制主義》、哈耶克之《到奴役之路》——後者是他買來「自己送給自己」的生日禮物。一些後輩學人的著作,胡適也虛心閱讀,如周策縱之《五四運動史》、夏志清之《現代中國小說 史》等。
潘光哲指着客廳「頂天立地」的書架上最頂層一排的《大漢和辭典》介紹説,第一冊和其他諸冊,版本明顯不同。第一冊是作者贈送給胡適的日本原版,其他各冊都是台灣的盜版。可見,讀書人愛書如命,連胡適都會買盜版書。
一般的參觀者通常不太注意洗手間的設置。我發現,胡適故居的洗手間內,放置着主人使用過的洗髮液、沐浴液等日用品,全都是美國的產品。其臥室內的桌子上則擺放着一台短波收音機,在電視尚未普及的時代,胡適通過這台收音機來瞭解世界局勢,好幾場美國總統大選的結果,都是從收音機中聽到的。潘光哲說,這台收音機放入電池,仍可收聽短波節目。臥房內還有當時台灣難得一見的美式暖爐,南港的冬天陰冷而漫長,暖爐大有用處。
這些只是美國中產階級家庭尋常的生活用品,但在當時的台灣,堪稱最高級的享受。胡適長期在美國生活,有過對現代文明的切身體驗。蔣介石和毛澤東都沒有這樣的體驗,梁漱溟和錢穆也都沒有這樣的體驗,他們的政治立場、思維方式、文化觀念以及對國家未來的想像,都與胡適迥然不同。
在胡適心目中,對於如何讓所有同胞過上現代、文明、自由、豐裕的生活,有着美好的想像與切實的規划。可惜,戰禍瀰漫、赤潮洶湧的現代中國,並未提供給他一展身手的空間與時間。
中研院是一個做什麼的機構?
二零零三年,我第一次訪問美國,專程去愛荷華大學探訪聶華苓女士。作為碩果僅存的《自由中國》雜誌的編輯,聶華苓給我談起了六十年代的往事,對胡適未去探望獄中的雷震頗不諒解。
而潘光哲根據新發掘出來的史料,又作出了一番新的闡釋:胡適一度想去探視獄中的雷震,身邊有人卻勸他不要去。對此,胡適不悅地反駁説,「這是我自己的事情,不由他人干涉」。然而,胡適最終未能成行,背後必定又有一番驚濤駭浪。那大概是學者們的一個新的考據題目了。
在二零一四年的太陽花學運中,中研院一批年輕學者成為學生們的「義務智庫」。總統馬英九赴中研院爲一個學術會議致辭,有學者進入會場舉牌抗議。由此,引發 關於中研院的地位及性質之爭論。
某些保守派指責説,中研院是總統的智囊,豈能反對總統?還有國民黨立委辱罵中研院變成了「太陽花研究院」,主張對黃國昌展開調查,甚至將其開除。
當我在胡適紀念館看到題為「胡適與蔣介石:道不同而相為謀」的特展時,發現胡適早已就「中研院是做什麼的機構」這個問題給出了答案。該特展細緻地描繪了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上的這兩位核心人物之互動、情誼與衝撞。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件事情是:一九五八年四月十日,中研院舉行胡適就任院長及第三屆院士會議之開幕典禮。蔣介石出席並發表講話,盛贊中國傳統倫常道德。主張全盤西化的胡適當場表示異議,認為蔣的說法「是錯誤的」。蔣介石氣憤之至,在當天的日記中謾罵胡適「真是一狂人」。
這就是知識人之風骨。中研院雖然得到政府財政之支持,但其研究是爲增進大眾之福祉,而非充當獨裁者之御用鷹犬。
如今,面對保守反動人士之壓力,中研院發表了一份擲地有聲的聲明,其中有一段如是説:「學術研究無法自閉於象牙塔中,需走入人群,與國家發展和社會脈動相結合,實踐人類對永恆價值的追尋。學者依其學術研究與知識探索所獲得之確信,提出具體主張,應享有言論自由之保障,此恆為民主社會之常態。本院作為公立研究機關,本於維護學術研究不受特定立場干預,就個別研究人員的言論,向來尊重多元,兼容並蓄。」
這份聲明,傳承了蔡元培和胡適開創的自由思想之風。在當下台灣民主嚴重倒退的時刻,中研院適切表現出應有之格局。當年,身為中研院院長的胡適,在蔣介石的壓迫之下,抄錄顧炎武的詩「遠路不須愁日暮,老年終自望河清」來自勉,若讀到這份半個多世紀後的聲明,定可含笑於九泉之下。 「自由中國」與「自由台灣」的願景,需要兩岸新一代公民的共同努力。
作者:余杰(中國旅美獨立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