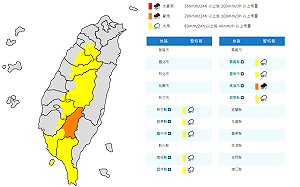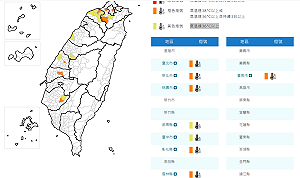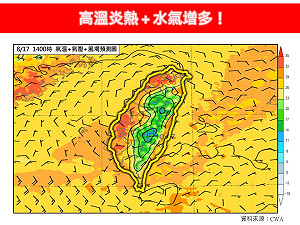在充滿碎片化資訊與即時輿論的年代,政治語言常被借用、改造,甚至被拔擢成超越歷史脈絡的萬用比喻。藍營偏好「抗戰」,不喜歡政府使用「終戰」,「雅爾達共識」正是近來討論川普與普丁在阿拉斯加會面的熱門詞彙。有人將川普與普丁之間的互動解讀為一種準雅爾達式的安排,彷彿只等澤倫斯基簽字畫押,戰爭便能立刻「殼平」。這種說法看似擲地有聲,實則不倫不類:既誤讀歷史,也稀釋了侵略與防衛之間的倫理界線,更以「共識」之名為現實政治的權衡與交易披上一層道德化的外衣。
歷史校正 強人迷思與責任邏輯
精選報導:吳恭銘觀點》危機四伏!立法院法制局報告下的憲法挑戰 罕見的政治企圖
雅爾達不是藍白想的那種「共識」 ,雅爾達會議是二戰末期「同盟國彼此」的戰後分工與秩序安排,參與者共享對軸心國的勝利與責任,不是侵略者與被侵略者的談判桌,更不是第三方替受害者裁決命運的審判席。把今日的雙普會比擬為「新雅爾達」,等於把侵略行為包裝為地緣政治的合理討價還價。起點錯了,結論必然歪斜:歷史提供的是規範與邏輯,不是任意挪用的修辭素材。
把侵略與調停混為一談,是二次傷害,俄羅斯入侵是在國際法上構成原犯罪,任何「促和」若以壓低受害國代價為前提,名為和平,實為替侵略開價。調停可以是善意,但不能取代被侵略者的意志。當論者以「新雅爾達」架構敘事,責任邏輯就被稀釋:加害與受害、侵略與自衛、調停與施壓,全都混成灰色,最後只剩「趕快成交」的功利算盤,加深川普出賣盟友的疑美論說法,鋪陳棄台論述。
歷史不容偷換 「共識」不是魔法
國共喜歡談「共識」,「共識」就是通關密語,「九二共識」就是虛擬的催情藥。雅爾達會議的本質,是二戰末期同盟國領袖為戰後秩序所作的高層協商,參與者共享的是對納粹德國與軸心國的戰時目標與戰後安排。這是一場「勝利者之間」的分配與安置,不是侵略者與被侵略者的談判,將雙普會比附為「新雅爾達」,等於將侵略行為合法化為一種地緣政治的「談判籌碼」,忽略了國際法對主權、領土完整與不侵略原則的明確規範。歷史的場景不同、角色位置不同、正當性來源更不同,強行類比,只會扭曲判準。
然而,當論述暗示川普邀請普丁出面,是美國低頭背棄盟友的不可信,這其實將多邊、長期且高摩擦的衝突簡化為兩個強人之間的交易,間接推論美國會背叛臺灣,拿臺灣與中共交易。戰爭之所以難以終戰,常常不在於缺少握手的畫面,而在於缺少可持續的安全安排、可信的履約機制與受影響方的實質參與。
和平的技術細節比宏大敘事更關鍵
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是單邊且持續的軍事行為,直接違反《聯合國憲章》的基本原則。將川普的「邀請」或任一政治人物的「調停」等同於「新雅爾達」,模糊了加害與受害、侵略與自衛、談判與壓迫之間的界線。調停可以是善意,但不能凌駕於被侵略國的意志;倡議和平可以是必要,如果所謂的「共識」建基於「讓受害者吞下更大的讓步」以換取暫時安穩,這樣的和平其實是延遲的衝突。
語言會塑形政治現實,這些人在暗示臺灣將被強權交易。將雅爾達作為修辭支點,會不知不覺地把「強權協商分配」正當化,使人們習慣於以「勢力範圍」的坐標理解國際秩序,而非以規則與權利為基準。當我們將戰爭的終局交給「兩人之間的共識」,就會忽略戰爭的多層次結構:烏克蘭的主權訴求、歐洲安全的縱深、能源與糧食市場的外溢效應、全球南方的外交算計,以及國內政治對各國領袖的約束。把這些層次壓縮成一個「雅爾達式交易」,是對複雜度的抹除,也是對現實風險的輕忽。
回到今天的公共討論,我們需要的是對比喻的節制與對制度的偏好。當藍白以「雅爾達共識」包裝現實中的政治交易,媒體與評論者的責任,是拆解這種修辭如何塑造認知,並提醒讀者:和平不是戲劇性的單一時刻,而是枯燥但必要的制度工程。與其追逐「兩人定江山」的戲碼,不如追問:多邊保證如何落地?烏克蘭的主體性如何確保?違反國際法的行為如何被追究?這些問題的答案,遠比「類比是否華麗」更能改變戰場之外的現實。
眾所周知,藍營把川普與普丁套進「雅爾達共識」的框架,看似提供了一個簡潔的解釋模板,實則偷換了歷史與責任的邏輯。歷史不是隨手可取的修辭貨架,和平也不是兩句話的交易。若真要為戰爭尋求出口,請從制度化的安全安排、可信的監督與受害者的主體性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