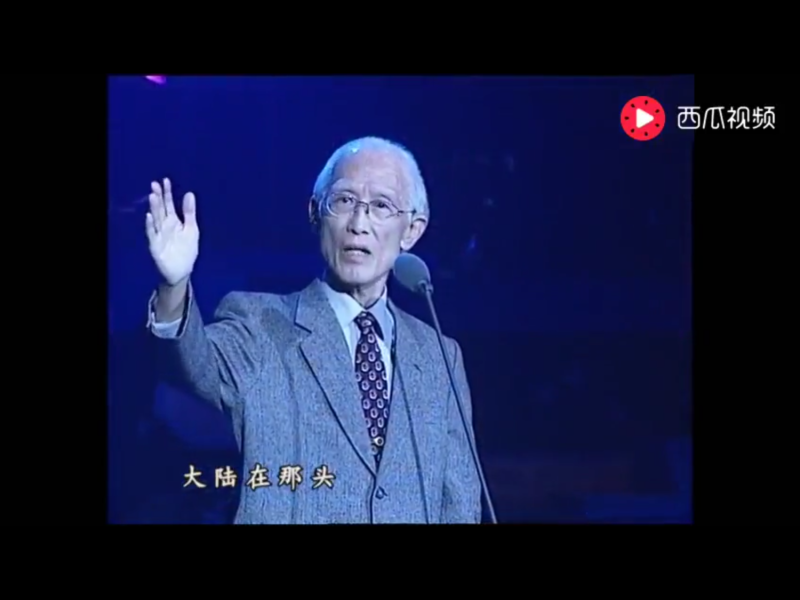政治,政治,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偽裝成正義。2017年12月14日,戒嚴時代就被黨國媒體譽為「詩壇祭酒」,還是國家文藝獎得主的余光中,以90歲高齡逝世。同樣在2017年過世的國家文藝獎得主鄭清文、李永平等人,都已拿到了總統的褒揚令,只有余光中至今尚未得此一蓋棺論定的殊榮。
也是國家文藝獎得主張曉風,認為余光中沒拿到褒揚令,跟管中閔迄今還沒當上台大校長的理由一樣,「都是政治不正確」。作家陳芳明則指出,文化部未幫余光中申請褒揚令,可能跟他長年支持前總統馬英九有關。
全站首選:高市議會藍營為「土方之亂」尋解方 柯志恩促中央精進法規
張曉風認為余光中沒拿到褒揚令,「不是他的損失,而是政府和社會的損失」,「歷史會給他一個肯定」。陳芳明則認為作家可以有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但「文化應該超越政治」,對於余光中這樣重要的文學家,政府不應保持「高度的沉默」。
總統府發言人黃重諺則在3月12日指出,褒揚令的頒發是依據「褒揚條例」等法規依法辦理;只要符合相關法令規定,由各單位依法申請,總統府就會依法頒發。過去2年京劇大師顧正秋、書畫大家王攀元、張光賓等人,過世後都有拿到褒揚令。文化部的回應則未提到是否曾為余光中呈請總統頒發褒揚令。
其實張曉風與陳芳明應該也都知道,余光中一生最大的爭議,絕對不是他戒嚴時代「御用詩人」的政治立場。即使解嚴後多年,他都敢在總統大選前夕,為了諂媚吹捧周美青,寫了根本就是打油詩的〈某夫人畫像〉,誰會不懂或在意他的政治立場。褒揚令該不該發,爭議原因當然還是余光中自己晚年都羞於再提的「狼來了」。
「狼死為大」的歪理
對4到6年級生來說,余光中是我們最熟悉的詩人之一。戒嚴時代的國中課本裡,能出現的現代詩,除「死了最安全」的楊喚,就是這位熱愛當權者,也被當權者熱愛的余光中。
本魯也熱愛余光中的詩文,除了馬屁過了頭的〈某夫人畫像〉以外。梁實秋曾讚美余光中:「右手寫詩,左手寫文,成就之高,一時無兩。」無論有沒有那張褒揚令,余光中左右開弓的才情與活力,在無論什麼立場上書寫台灣文學史,都不可能漏掉專屬於他的特定篇幅。
回憶1970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本魯對余光中的政治立場與文學見解,也無特別的異議。文革那十年左膠自以為是的「革命」言論,如今在香港回歸中國後,當權者與當事人也都避而不談了,在台灣也不會有人再關心余光中當時的政治立場。
但在台灣經歷過戒嚴時代的人都了解,很少有人敢對(還要能對)當權者說「不」的。就像洪秀柱尊翁,被鷹犬誣陷而繫於囹圄,無論說了什麼或做了什麼,甚至出獄後要定期報告什麼,都不應苛責,也無須深究。
但無法說「不」,不代表就可以主動,甚至是積極在做這些事。在個人安全無虞下,只為私利或私怨,就主動積極地充當「抓耙仔」,例如馬英九在美擔任職業學生,只要你曾幹過這種齷齪勾當,沒有什麼「狼死為大」的歪理。即使挫骨揚灰,歷史仍要追究,不然轉型正義就是在放屁。
所有爭議都在於「狼來了」
雖然李敖或許是基於私怨,曾嚴厲批評余光中「文高於學,學高於詩,詩高於品」,「一軟骨文人耳,吟風弄月、詠表妹、拉朋黨、媚權貴、搶交椅、爭職位、無狼心、有狗肺者也」,「過去反共,現在跑回中國大陸到處招搖」。但這些激烈言詞,用來形容其他作家,也許都適用,甚至也不影響其受褒揚。因此說來說去還是那句話,「狼來了」成了余光中一生最大的汙點。
戒嚴時代的作家,都是住在玻璃屋裡。立場與見解不同時,吵吵鬧鬧甚至大打出手都行,然而在任何狀況下,都不能丟出石頭。否則傷及無辜不說,覆巢下自己也未見得是最幸運的完卵。
1970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其實朱西甯批得更早。1977年4月號《仙人掌雜誌》的〈回歸何處?如何回歸?〉裡,他就質疑「在這片曾被日本佔據經營了半個世紀的鄉土,其對民族文化的忠誠度和精純度如何?」
朱西甯批評鄉土文學,不僅比余光中8月20日才在《聯合報》上發表〈狼來了〉更早,而且還是站在統獨(中日)差異的立場去批的。今日的台派或獨派覺青,反統的立場很堅定,但是左是右卻不一。因此余光中只是站在左右對峙的立場去批鄉土文學,照理說朱西甯比余光中更「反動」,但現今批朱老的不多,箭頭全往余光中的〈狼來了〉這裡來。
行禮如儀的官樣文章
余光中在〈狼來了〉裡,無厘頭的栽贓台灣的鄉土文學,就是中國的「工農兵文學」,其中若干觀點和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竟似有暗合之處」。這句在陳明成筆下稱為「血滴子」的利器一出,立刻「在文壇弄得風聲鶴唳,瀰漫著肅殺的血腥氣息。」
比「血滴子」更可怕的武器,是余光中直接對當權者指控特定對象,也就是當時剛出政治獄不久的陳映真。陳芳明《鞭傷之島》裡〈死滅的,以及從未誕生的—評余光中、陳映真道路的崩壞〉就提到:
「我收到余光中寄自香港的一封長信,並附寄了幾份影印文件。其中有一份陳映真的文章,也有一份馬克思文字的英譯。余光中特別以紅筆加上眉批,並用中英對照的考據方法,指出陳映真引述馬克思之處。」
當事人陳映真對於陳芳明《鞭傷之島》裡余光中向王昇密告,在《聯合文學》二○○○年九月號的〈關於臺灣「社會性質」的進一步討論—答陳芳明先生〉也說:
「事隔多年,而且因為陳芳明先披露了,我才在這裡說一說。余光中這一份精心羅織的資料,當時是直接寄給其時權傾一時、人人聞之色變的王將軍手上,寄給陳芳明的,應是這告密信的副本。余光中控訴我有『新馬克思主義』的危害思想,以文學評論傳播『新馬』思想,在當時是必死之罪。據說王將軍不很明白『新馬』為何物,就把余光中寄達的告密材料送到王將軍對之執師禮甚恭的鄭學稼先生,請鄭先生鑑別。鄭先生看過資料,以為大謬,力勸王將軍千萬不能以鄉土文學興獄,甚至鼓勵王公開褒獎鄉土文學上有成就的作家。不久,對鄉土文學霍霍磨刀之聲,戛然而止,一場一觸即發的政治逮捕與我擦肩而過。這是鄭學稼先生親口告訴我的。在那戒嚴的時代,余光中此舉,確實是處心積慮,專心致志地不惜要將我置於死地的。」
余光中當時的手段與心態太可議,使他日後自己也心虛,結集出版時從不收錄〈狼來了〉,訪談他的傳記裡也完全迴避這一話題。因為陳映真當時才出獄二年,管束期間涉入匪諜案必罪加一等,這是人命關天的大事。朱西甯與王昇之間的關係,絕對勝過余光中,但朱西甯不曾用過余光中這麼下流的手段就是了。
坦白說總統的褒揚令,向來也就是行禮如儀的官樣文章;比余光中更不堪的黨國鷹犬,只要媒體不緊盯,不也照樣就發了。若大家這麼在意,就施捨一張褒揚令給「狼來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