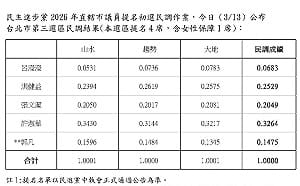母語、農權、台灣國!耀伯一生的夢想與奮鬥目標。這一路走來的心路,化做一篇篇文章,耀伯要出新書了,預計11月由玉山出版社發行,感謝所有人的一路扶持,更感謝所有支持耀伯新書的好友們。
「喂,蛤啊,抓到戴振耀!他媽的,明天就要結案了,這傢伙跑出來幹什麼?」正在偵訊許天賢牧師的外省籍情治主管,突然被喚有電話,不耐煩起身走到牆邊的電話桌,拿起電話後,對著電話筒大呼小叫。
許天賢,1951年6月生,台南神學院畢業,美麗島受刑人之一。1979年12月23日,基督教最重大日子,聖誕夜的前一天上午,許天賢正在嘉義林子內教會,主持聖誕節讚美禮拜,卻遭到四位情治人員,無視信徒的驚呼,以及通融完成禮拜的請求,強行從講壇上架走。
此事件引發教會公報以頭版規格,刊出強烈抗議與譴責,指出即使是德國希特勒政權,要逮捕反抗希特勒的神職人員,也不敢進入教堂,而是在教堂外等待禮拜結束後才進行拘捕。
但是,對於如此強烈的譴責,國民黨毫不在意。許天賢在獄中受盡刑求之苦。最後跟戴振耀一樣,被判3年徒刑。
入獄前,戴振耀與許天賢在許多美麗島活動有交集,但實際上兩人並不相識,後來在獄中相識,才從許天賢口中,聽到偵訊室裡的這段電話對話。當時許天賢心裡在想,「戴振耀是誰?真可惜,再躲一天就好了。」
全站首選:伊朗新最高領袖首度發聲!「不會放棄復仇」將繼續封鎖荷姆茲海峽
戴振耀是繼施明德之後,最後被捕的受刑人。第一站到岡山分局,都是平日熟識的員警,在這裡只是進行一些資料登記,還有員警請抽香煙,緊張不安的情緒舒緩不少。很快的,第二站轉送到刑警大隊。
「這什麼案?」一位女警納悶的口吻,詢問帶戴振耀進刑警大隊的男警。可能是因為戴振耀一臉純樸,服裝老實,戴眼鏡更顯斯文,不像經常出入刑警大隊的黑道份子。
「叛亂!」身旁的男警,吐出簡潔的兩個字。
突然聽到都是四聲重音的叛亂二字,戴振耀開始感受到壓力。接著又是一連串的個人資料確認,還有照相,正拍、側拍。筆錄的進行,也比在岡山分局恐怖許多。沒想到,更恐怖,簡直生不如死的痛苦,等在後面。
清晨被捕,最後被蒙著眼睛,手銬腳鐐,轉送到高雄夀山深處的「南警部」,已經黑天暗地。這裡被劃為軍事重地,即使是在地高雄人,也難以一窺究竟。
「鼓打過來、鼓打過來。」鐵柵門內多位受刑人,看見戴振耀一進門,手伸出,不斷呼喊。
「鼓?啥米意思?」戴振耀一頭霧水。入監後才知道,原來「鼓」是香煙的意思。如果看起來有吃檳榔,就會被喊「金龜」擲過來。
還在不明所以之際,已經錯過了身上香煙的最後剩餘價值。因為緊接著,戴振耀被脫到只剩一條BVD內褲。
深夜被推進一間約五坪大,躺了大約十人上下的囚室。原本大多已睡著的囚犯,因為鐵門打開,聲響大作,有幾個人睜開眼睛,反射動作的將臉龐朝向鐵門方向。戴振耀一眼就看到被吵醒的囚犯裡,有位認識的辜水龍先生(鳳山市民代表)。
囚室裡,唯一的設備是馬桶,沒有床、沒有任何棉被、衣物,所有人都光著只穿一條內褲的男性肉體。更醒目的,是牆邊排著一碗飯配一碗水,有好幾組,讓戴振耀誤以為是祭拜的物品。
「水龍兄,這擱要拜床母逆(這裡也要拜床母嗎)?」戴振耀忍不住問。
「噓!」辜水龍暗示不要多話。獄警離開之後,才知道,那是他們每天僅有的食物,飯跟鹽水。南警部的「鹽水大飯店」之名,由此而來。
整個囚室,只有戴振耀跟辜水龍是美麗島案。其他大部份是走私犯或刺龍刺鳳的黑道份子。一月中旬畢竟是冬天,即使是高雄,又在山上,所有人只穿一條內褲,直接睡在地上,感冒發燒的情況很嚴重。
睡覺時,當然也不可能有枕頭,大部份人都是彎著手肘當枕頭,身上唯一的遮蔽物,是獄方發下來的大型粗質塑膠袋,大小如麵粉袋。那個年代,還沒有垃圾袋這種東西。因為無法遮蓋全身,躺地而睡的囚犯,都會不自覺的縮著身體。
戴振耀跟辜水龍的待遇,比其他刑事案件的人更嚴苛,完全不能「放風」(到戶外走動),也不能去「福利社」。還有不定時的反覆偵訊、刑求。偵訊都挑深夜,差不多凌晨一、兩點正好睡的時候。
「XXXX,起來!」兩、三個憲兵打開鐵門的同時,一邊大喊編號,不會叫姓名。只剩內褲的戴振耀,手銬腳鐐的狀態被押出去。憲兵帶著附刺刀的槍走在兩側或身後,沈重的腳鐐拖著走路非常痛,必須用戴手銬的手,拉起長鍊的腳鐐,才能勉強減輕疼痛。
「阿耀,你千萬毋通矜(不能供出)別人喔,卡忍耐咧!」關在隔壁的蔡精文,看到戴振耀第一次被押出牢房,非常懇切而鄭重的叮嚀。
悔過書?想到郭國基、余登發
第一次被憲兵叫醒押出去,掛著少校銜的檢察官戴銀生,一見面就惡狠狠的,丟筆丟紙加上拍桌子,吆喝著寫悔過書。戴振耀想著余登發、郭國基「絕不屈服」的身影,期許自已也不能丟臉。
「我們以前在學校參加遊行,也是拿火把、拉布條、喊口號,結束時教官還會發獎品,現在這個(世界人權日遊行),有犯什麼法嗎?」戴振耀一心想堅持尊嚴,但也不敢太逞強,僅以試圖講道理的聲調,囁嚅的說這幾句話。
「他媽的,你想當英雄是不是,等一下就讓你當狗熊。」年齡跟戴振耀相當,大約三十歲出頭的外省籍檢察官戴銀生,或許原本預期要看到認錯求饒的黨外份子,不料竟然如此不知好歹,頗為惱羞成怒。
究竟為什麼會有寫悔過書的機會?根據許天賢牧師聽到的電話對話,是否可以推論這個整肅計劃,因為施明德的頑強逃亡,已經拖延原訂時程太久,好不容易施明德落網,國民黨想儘速結案,進行起訴,並且速審速結,所以願意放過比施明德更晚四天才被捕的「小咖」戴振耀?
是否寫了悔過書,真的就可以免受刑求之苦,回家過年?這些疑問,在戴振耀拒寫悔過書之後,都不可能有答案了。
當年肅殺的氣氛下,拒絕寫悔過書的意志,來自親眼目睹余登發與郭國基,絕不屈服的身影典範,還有高中之後,大量閱讀,吸收自由主義思想,進而對自由主義與人性尊嚴,所產生的堅定信仰。
後來的偵訊過程,果然吃盡刑求的苦頭,不只檢察官戴銀生,動不動就邊罵邊打,年紀更輕一點的書記官劉偉森,甚至也會放下記錄偵訊的紙筆,離開座椅,跟著又踼又踹,仿佛折磨別人是他們這份工作最大的成就與樂趣。
後來在獄中,跟其他難友談到被刑求的狀況,每個人情況都不一樣,似乎愈早鎖定且被逮捕的,負責偵訊的刑求者,都是經驗老道,而且早已沒有人性的情治人員,讓被刑求者個個生不如死。
刑求!人間煉獄
戴振耀覺得最慘無人道的,是林義雄、紀萬生、邱奕彬的遭遇。偵訊室裡不斷上演的,根本就是人間煉獄,很多人到最後簽自白書時,根本都不知道自已到底自白了什麼,一心只想求死,一了百了,結束生不如死的痛苦。
戴振耀比較晚被逮捕,分配到的少校檢察官相對菜鳥,年輕力壯打起來很痛,但刑求花樣不多,也或許是道具不夠用。除了被毒打踹踢之外,曾有的花樣是戴著手銬的雙手,被吊到一定的高度,想避免手痛,就必須墊著腳尖支撐,但是腳酸無法維持墊腳尖時,雙手就會因為拉長跟腳的距離,而被鐵銬拉得非常痛。
單單維持這個姿勢已經很痛苦,每每回答無法讓戴銀生滿意,不是拳頭過來,就是被原子筆用力戮刺背部,那時有生不如死的感覺。但後來在龜山監獄與紀萬生老師同牢一年,才知道什麼才叫正港的生不如死。
紀萬生是被逮捕的第一批,歷經各種花樣的刑求道具,坐飛機(雙臂撐開做展翅狀,再猛打腹部)、老虎凳(長期被綁在鐵椅上固定,連睡覺、大小便,都不得動彈)、蒙古烤肉(香煙燒臉頰)、鼻孔灌辣椒水、乒乓球塞嘴巴,左耳被打聾,臉也被打到歪。
此外,到了獄中也證實老爸戴清連的見解正確,「絕對袂賽(不能)相信國民黨」,新聞不斷報導說「政府寬大為懷,盲從份子自首,從輕發落」,都是假的。很多主動投案自首的,依然遭到慘無人道的刑求。
邱垂貞就是在「政府寬大為懷」的催眠下自動投案,卻不知後面還有一個條件是「無知盲從」,而認定權完全在國民黨。邱垂貞被毒打到胃出血,老虎凳坐了十天,被逼寫自白書,一遍又一遍,疲勞轟炸連續達四天四夜不能睡覺。
邱垂貞,1951年生,因為曾在美麗島服務處舉辦的群眾活動現場演唱禁歌「望春風」,而成為具有台獨意識的罪證之一,他是將台語歌曲引入反對運動的代表性人物之一。1992年立法院首次全面改選,當選桃園選區立委。曾聘任野百合學運領袖之一的鄭文燦為立委助理。
更離譜的,還有劉華明的例子,劉是屏東人,哥哥劉泰和當時很相信電視、報紙、廣播不斷強調的「政府寬大為懷」,於是勸導劉華明去自首,並且陪同去警察局。結果,兩人都一起被抓進去。劉泰和是當年極少數在最後被判無罪者之一,但早已歷經刑求之苦。
劉泰和曾是台灣獲獎的健美先生,當年在健身界頗負盛名,專注於健身事業,跟美麗島毫無瓜葛,更未參加國際人權日活動。只因為陪弟弟自首時,搞不清楚狀況,詢問「那我也要作筆錄嗎?」居然這樣就一起抓進去「作業績」。
當時偵訊大多是個別進行,但戴振耀剛入獄不久時,可能「叛亂犯」實在太多,偵訊室不夠用,一次半夜被押進偵訊室,看到同樣全身只剩一條內褲,跪在牆邊全身發抖的劉泰和,膝下橫著一根報夾棍(夾報紙方便掛架的木條),身上多處被毆打的傷痕,雙手拖著厚重的精裝書,而且必須高於頭頂。
劉泰和再三解釋他與美麗島毫無干係,但是,事實、法律、證據,似乎一點都不重要,硬是逮捕入獄,用刑求要自白,而如此要到的自白,在法庭上徹底不堪一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