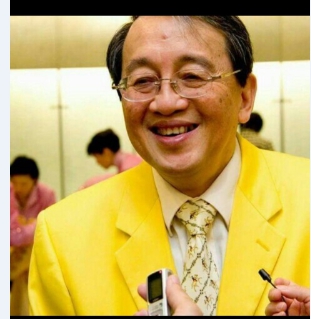新認識的朋友惠蘭出了一本畫集,題為「在豔陽下孵夢」。我不是藝評家,對繪畫的歷史、派別沒有太多概念,對繪畫的技巧一竅不通,更糟糕的是我辨色力還不太正常,但這絲毫不影響我長年對不同藝術的興趣。其實,讓我著迷最深的藝術,是一個個不同生命的完成。每個人依不同的境遇,以不同的秉賦、不同的努力,雕琢自己的生命。有的人的一生豐潤圓滿、有的人困頓顛躓、有的人渾然天成,有的人嘎然而止,作為人生藝術家,每個人都留下不同的生命作品。
有人說,「人生是選擇的總合」。對許多在人生場合瞻前顧後、苦思細想,然後勇敢堅決或怯懦被動做選擇的人來說,這講法蠻貼切的。可是我知道許多藝術家,他們之從事創作,彷若天喚(德文說Beruf,英文說vocation),追隨的是一股起自心中、無可抑遏的動力,幾乎沒有做其他選擇的餘地。我讀舒伯特、讀杜普蕾(du Pré)、讀梵谷等等的傳記,都有很強烈的這種感覺。我認識一位台灣畫家,在聚會的場合總是一隻碳筆不停地素描,我每每都被那股背後莫名的力量所震攝。事實上,在我的行業裡,有些天生的記者,也是同樣被一股永不終止的好奇心所驅使,有時候甚至飛蛾撲火。
惠蘭所受的不是最正統的美術教育,但她的画作已經兩度入選巴黎春季沙龍。我很奇怪她是怎麼做到的。她的回答讓我感到意外。她說,高中時她半工半讀,晚上在「中正紀念堂」附近的照相館裡幫忙洗照片。那是社會遽變、街頭狂飆的年代,一些報社攝影記者都在她的照相館趕截稿前的照片。她時常為這些影象內心波動不已,尤其是看到鄭南榕自焚後的照片,更是受到震撼。她因此有強烈想為台灣做點事的心願,既然沒有其他技能,只是愛畫画,就拼命地畫,希望有一天為台灣增光。
雖然「愛台灣」也是一種動力,但我總覺得好的藝術需要一個比「愛國心」或「責任感」更直接、更原始、更勇猛的驅動力量。惠蘭無疑是具備這種力量的,只是她還不曾自覺地把它表述出來。
惠蘭有一股強烈的欲望,要把內心的感覺表達出來,我第一次和她在桃園機場碰面時,便是這樣的印象。她所找到最深沉,卻也得心應手的方式是透過色彩、運用圖像,盡情地畫画。音樂沒有成為選項,因為身體先天的限制。
這也稍可解釋她的画冊中,除了較早期(2000年)一幅「秋日流水」是比較中規中矩,反映眼見景象的印象作品外,其它所有画作幾乎都強烈表達畫家主觀的意象,是心情、是氛圍、是意境。
2003年前後似乎是畫家無比快樂的日子,或許是被歐洲繽紛的采姿所眩惑,幾幅有關巴黎城市的繪作,還有以豔荷、春雪為題的作品,都有醒目的線條和亮眼的色塊,尤其黃色的大膽運用,讓作者內心的愉悅完全無法掩飾。
這種直接、毫無禁忌的黃色在2005年以後的作品裡不見了,稜銳的線條也逐漸消失。不再是顏色的對比爭豔,更多是以墨綠、暗紅和紫藍為基色的氣氛蘊染。畫家似乎沉迷在色彩的奧秘裡,恣意探索光線的細微變化。這種對光線的著迷最開始顯現在2004年的「挪威伯恩港口」,這幅由2003年寫生重畫的作品簡直就像一座色彩的博物館。

惠蘭2007年以後的作品似乎趨向寧靜或簡約,也更成熟。「雨中威尼斯」場景不小,但用筆精練,很有雨中朦朧的氣氛。「心花」構圖簡單,卻意境深遠。「月光下的白荷」畫的是宜蘭的星空,讓我想起海德堡的古堡廢墟,半夜星空下,城牆上彷彿有精靈在跳舞。形成例外的是2009年的「春天」,繁複的床褥飾摺和背景,似乎是反映畫中貴婦心情的波濤起伏。
2008年惠蘭在人生路途上碰上大石頭,拌了一個大跤。我很喜歡她在畫冊序言中所說的一句話,她說,站在大石頭上,看到的人生風景更壯麗。惠蘭2003年入選巴黎春季沙龍的作品,画題便叫作「聽見花開的聲音」。這樣的題放在惠蘭的画上,特別具有意義。惠蘭用一顆敏感而樂觀的心,渴望而終於聽見了花開的聲音。我相信,用同樣這顆心,她也一定可以實現所盼望的壯麗人生。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