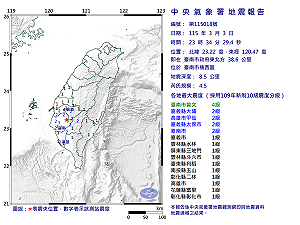深夜十一點,宿舍裡的燈光昏暗。我的手指熟練地在播放器設定鍵點開「播放速度」,選擇「2.0x」。原本悠揚的電影配樂變得滑稽,演員深沉的獨白成了尖銳的快口。不到幾分鐘,我「看完」了一部兩小時的藝術電影。接著,我又點開了幾個標題為「五分鐘帶你看完某某影集」的解說影片,讓「大壯與小美」的公式化旁白快速填充我的腦袋。
那一刻,我感到一種掌握時間的成就感。但當我關掉螢幕躺在床上時,一種巨大的空虛襲來:我記得劇情大綱,卻記不得主角的神情;我省下了時間,卻想不起任何一點感動。作為一名學習媒體批判的大學生,我意識到這枚「2.0x」按鈕並不代表自由,而是一場對感官與主體的雙重剝削。
一、 文化工業的標準化:當藝術淪為零件
法蘭克福學派的阿多諾(Theodor Adorno)曾嚴厲批判「文化工業(Culture Industry)」,指出大眾文化產品正趨向標準化與公式化。當代氾濫的「電影解說」與「倍速播放」,正是文化工業的極致表現。
在阿多諾看來,藝術的價值在於它的獨特性與挑戰性。然而,當我們選擇以兩倍速觀看,或依賴五分鐘的「懶人包」時,我們其實是在配合一套工業系統,將藝術品拆解、壓平,最後降級為純粹的「資訊」。原本導演精心安排的長鏡頭、配樂中的呼吸、演員細微的顫動,這些需要「時間」來發酵的感官體驗,在倍速之下全部成了多餘的雜訊。我們獲得了劇情的「零件」,卻失去了作品的靈魂。這就像是為了快速止餓而直接吞下壓縮餅乾,我們雖然獲取了熱量,卻永遠體會不到烹飪的層次與食物的溫度。
二、 單向度的人:被效率綁架的工具性思維
為什麼我們在休閒時仍感到焦慮,非得「省時間」不可?馬庫色(Herbert Marcuse)在《單向度的人》中提出了深刻的警示。他認為在發達的工業社會中,人類逐漸喪失了批判與否定的能力,轉而追求「工具性」的效用。
當代大學生的社交圈節奏極快,「看過某部片」不再是為了自我成長,而是為了獲取「談資(Social Capital)」。為了在午餐談話中不掉隊,我們追求最快、最直接的資訊輸入。馬庫色所擔心的「單向度」在我們身上精準體現:我們只關心「這部片演了什麼?我有沒有談資?」,而不再關心「這部片帶給我什麼思考?」。我們成了追求效能的機器,甚至連娛樂都要求有「產出」。這種對效率的病態追求,讓我們在數位海洋裡瘋狂打撈資訊,卻在精神的荒原中枯萎。
三、 數位窮忙:省下來的時間去哪了?
最諷刺的莫過於這種「數位窮忙」。我們透過倍速播放省下的那一個小時,真的讓我們過得更從容了嗎?現實是,當大腦習慣了高頻率、快節奏的資訊輸入,我們的耐心也隨之萎縮。
那些省下的時間,往往並沒有轉化為更高價值的產出,反而被投入到了更碎片化的短影音循環中。我們習慣了兩倍速的多巴胺刺激,導致我們無法再忍受任何「慢」的東西——無論是艱澀的經典文學、需要鋪陳的慢電影,還是現實生活中那些無法快轉的難題。我們以為自己在省時間,其實我們只是在浪費更多時間去進行無意義的數位流浪,陷入了一種「越省越忙、越忙越空虛」的死循環。
奪回對時間的感受力
作為大學生,我們正處於感官最敏銳的階段。如果我們連欣賞一齣戲、讀一段文字的耐心都被技術剝奪,我們又該如何去處理現實生活中那些無法「快轉」的關係與困境?人際關係的磨合、自我價值的探索,這一切都沒有「解說版」。
我想,是時候對這種「效率至上」的邏輯發起微小的抵抗。這不僅是觀影習慣的改變,更是一場奪回主體性的實踐。試著在某個週末,關掉倍速,放下手機,讓情緒在緩慢的節奏中完整地起伏一次。當我們不再急著抵達劇情的終點,我們才真正開始擁抱生活。別讓追求效率的焦慮,殺死了我們感知世界的能力。生活不該是一場快轉的賽跑,而是一場值得慢慢品味的長途旅行。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