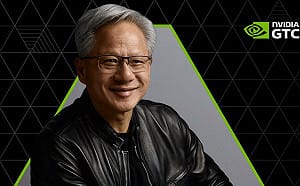香港學者饒宗頤去世後,中聯辦在其官方網站發布消息表示,“國家主席習近平、總理李克強、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政治局常委汪洋、副總理劉延東、國家副主席李源潮、政治局委員楊潔篪、中央組織部部長陳希、前國家主席胡錦濤、前政治局常委劉雲山、前中紀委書記王岐山等中央領導以不同方式表示悼念,並向其家屬表示慰問”。中聯辦主任王志民當日即到饒宗頤家中慰問悼念,次日再度到饒宗頤家中,“轉達國家主席習近平、總理李克強等國家領導人對饒宗頤先生的逝世表示悼念,對其家屬表示慰問”。中國央視更是對其極盡讚譽之詞:“饒宗頤先生畢生學術耕耘不輟,藝術創作不止,文化傳承不斷,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弘揚者,「一帶一路」文化傳播的踐行者,是中華文化自信的表率。他的學術造詣、藝術成就和國家情懷受到廣泛稱讚,他是香港的自豪,也是國家的驕傲。”甚至形容饒氏之辭世爲“文曲星歸天”。更有媒體評論説,國家最高領導人對一名在海外生活的學者公開表示悼念,是「超規格」表現。饒宗頤的追悼安排,很可能會接近前政協副主席霍英東離世時的追悼規格。
饒宗頤生前常常説自己「喜讀書,不喜交際」。然而,已經九十多歲時,他偏偏不辭辛勞,遠赴北京“朝聖”,雖然沒有見到聖上,倒是見到了兩朝宰相——一次謁見溫家寶,一次謁見李克強。李克強在中南海紫光閣當面稱讚饒氏“近百歲高齡仍心繫國家發展,學術耕耘不輟,藝術創作不斷,是香港特區的驕傲”。當時,有北京學者認為,這或可視作繼習近平看望北京大學教授湯一介後,中共當局力圖推動傳統文化復興所釋放的又一訊號。
當前熱搜:獲徵召就鬧事! 藍動員千人擠車站迎接游淑貞 作家傻眼:這是21世紀台灣嗎?
我對於共產黨捧的文人,首先就打一個大大的問號。因為共產黨不會輕易投入資源塑造“國學泰斗”,除非這個“國學泰斗”有益於其統治。從共產黨對待劉曉波和饒宗頤截然不同的態度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不屈服的異議者,一定要囚禁、虐待致死,讓他人望而卻步;曲學阿世的乖乖綿羊,則可樹立爲奴才之樣板,讓後繼者絡繹不絕。
饒宗頤從來不是遺世獨立的世外高人。香港評論人古德明指出,饒氏雖故作清高,但香港達官貴人聚會,常常見他身影。他更事君有道,深得中共歡心。二零一七年,香港易手紀念日前夕,他告訴《廣州日報》記者:「香港回歸祖國懷抱那天,我心情激動,作《臨江仙.賀香港回歸》一詞。」二零一三年,習近平提出「中國夢」不久,他又撰《中國夢當有文化作為》一文響應。中共當局對於這些言行舉止,當然是看在眼中,樂在心頭。
饒宗頤除了與現任特首林鄭關係密切之外,與香港的建制派人士也關係友好;他是全國政協副主席兼前特首董建華牽頭成立的“團結香港基金”之名譽顧問,過往亦至少兩度捐出墨寶予中共在香港的傀儡政黨民建聯拍賣籌款。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在民建聯於二零一四年舉行的籌款晚宴上,拍賣饒宗頤的兩幅墨寶,分別籌得兩百萬及一百八十萬元。時任中聯辦主任張曉明首度公開拍賣書法作品,為民建聯籌得一千三百八十萬元,加上他獻唱一曲《敢問路在何方》另籌得一千一百萬元,讓饒氏望塵莫及。事隔兩年,民建聯再舉行籌款晚會,饒宗頤同樣捐出墨寶支持,但「只籌得」三百萬元。張曉明的字畫成交價高達一千八百八十萬元。學富五車的泰斗被不學無術的貪官打敗,真是大大“有辱斯文”,不知饒氏當作何感想?香港學者蔡子強評論説,饒宗頤墨寶的藝術價值肯定較張曉明的書法為高,然而“捐款者以高價競投張曉明的作品,是希望討好民建聯與中聯辦”。可見,共產黨雖然用他,亦不過“倡優蓄之”,共產黨官僚及親共的香港商人,並不是真心尊重其學術成就及書法藝術,真是自取其辱。
當前熱搜:伊朗彈道飛彈轟土耳其!遭北約防空系統摧毀 恐觸第五條款
當代中國的“國學熱”,並非自然生成的,而是官方可以引導的。其源頭是六四屠殺之後中國出現信仰及文化真空,中共當局深知馬列毛主義對大眾失去了吸引力,只好重新抬出文革中被毛澤東摧抑的傳統文化,即譚嗣同所説的“兩千年皆秦制”,來蠱惑和麻醉人心。穿不倫不類的漢服、讀“弟子規”、召開全球佛教大會、乃至抵制聖誕節等“洋節”,甚囂塵上、蔚為大觀。於是,活得比同代人更長的季羨林熬成了“國學大師”。季羨林死後,家人爭奪遺產,醜態百出,顯示國學大師連“齊家”這個最低標凖都未實現。
由此,饒宗頤成了碩果僅存的“國學大師”。這倒符合“香港城邦論”的倡導者陳雲所説的“華夏文化的真傳在香港”。而台灣人對饒氏的尊崇,亦源於國民黨當年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以及國民黨長期的“中華文化中心主義”的洗腦教育。中華文化的神秘化和巫術化,在香港和台灣這兩個形式上已經實現現代化的社會,甚至比在中國更加嚴重。據說,饒宗頤冶學範圍極廣,涉及考古學、古文字學、史學、詞學、音樂史、目錄學、方志學等;且精通多國文字,包括英、法、日、德、印、伊拉克語等,並通曉梵文、古巴比倫楔形文字等——這些都是沒有多少人能懂的領域,不懂,人們自然就肅然起敬。饒氏的弟子汪德邁指出,饒氏的工作能力異於常人,更形容老師是一座「行走的圖書館」:「驚人的記憶力,是饒公成為卓越文獻學家的原因之一。」然而,實事求是地説,饒氏所做的僅僅是資料收集和整理工作而已,他並沒有任何一部作出獨特思想創見的著作。他精通多種文字且記憶力驚人,在古代農耕社會固然是一大特長,但在計算機和網路普及的現代社會,幾乎不具備多大的優勢。所謂「行走的圖書館」,難道比得上連小學生都會使用的維基百科和谷歌蒐索引擎嗎?
饒宗頤讀書固然很多,但沒有被真理所光照的知識,即便汗牛充棟、滿坑滿谷,也只是某種讓他可以“貨與帝王家”的資本積累而已,而無法形成可以“因真理、得自由”的思想和觀念。這就是西學與國學之根本性差異:西學從希臘和希伯來時代開始,就具備了強烈的“求真意志”,以探索人的自由和解放爲旨歸,故而西學能逐漸建構起普通法傳統、法治和契約精神、私有產權和人身自由的保障、代議制等近代文明的關鍵因素;而國學從春秋戰國時代開始,就是合縱連橫,奔走列國,以權術爲方法,以權力爲導向,所謂“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用學者黃文雄的話來說,不過是“帝王統治術、封建護身符、思想的麻藥、倫理緊箍咒”。
當儒學成為國學之主流之後,更是成為生產奴隸和奴才的流水線。黃文雄指出:“儒教強加在百姓身上的,如君君臣臣、夫婦有別,全是合理化社會不平等的奴才道德,大部分百姓雖無力反抗,也不可能真心接受,因此只要統治者管不到,就不會乖乖遵守,所以看在外國傳教士眼裡,自然是一群被動、缺少反省與良心的「良民」。至於少部分內化儒教道德、自願當奴才的臣民,為了顯示盡忠盡孝,便以忠孝節義之名,上演一齣齣父食子、夫殺妻、割股獻君、切肉餵父、易子而食的荒謬場景,終將中國社會帶領至無以復加的變態、病態、畸形狀態。”對此,日本明治維新時代的思想家福澤諭吉感嘆説:“一個國家社會,若儒術越發達,儒學愈興盛,只會造成更大的惡,人們的智慧德行每況愈下,惡人與愚者大增,禍患無窮。”難怪福澤諭吉要竭盡全力帶領日本“脫亞入歐”——所謂“脫亞入歐”,其實是“脫華入歐”,也就是擺脫如硫酸般具有腐蝕作用的中國文化的影響,邁向自由獨立的西方文明。
饒宗頤是一名中了儒學之毒甚深的凡夫俗子、趨炎附勢之徒,在遙遠的帝國邊緣的香港,至多算是一名三心二意的“幫閑”,其作惡程度遠遠比不上那些在中國“擼其袖子蠻幹”的幫凶,如林毅夫、胡鞍鋼、余秋雨、于丹、莫言之流。饒宗頤得享長壽,得益於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的自由與法治的保障,否則,若他在中國,說不定熬不過反右、文革等疾風暴雨的政治運動,即便倖存下來,也沒有一間書房、一張書桌供他吟詩作賦。所以,他當感激的不是共產黨,而是英國人。
畸形的中國文化遵奉“人死為大”的變態原則,為什麼人死了就能享有免於被批評的豁免權呢?既然每個人(特別是公共人物)都需要“蓋棺論定”,那麽對死者的評論乃至批評就是理所當然的。我常常在某些公眾人物離世時發出“不和諧”的聲音,如季羨林、陳映真、楊絳,惹得很多他們的粉絲乃至為數眾多的“厚道人”不快甚至憤怒。但我堅持認為,既然他們在公共領域享受了讚譽,獲得了有形無形的資源,他們就必須付出接受多元評論乃至負面評論的代價。
饒宗頤當然不是大奸大惡之徒,若是他生長、生活在歐美社會,他不過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大學教授,他的學問固然有一定的價值,但不會像在華人世界那樣被視為“國寶”。美國沒有“國學”,也沒有對所謂“國學大師”的五體投地,美國是一個平等的社會,開餐廳的人並不會覺得自己比當教授的人低人一等,當教授的人也並不會覺得自己比開餐廳的人高一等。而華人世界對瑣碎的知識和人的記憶力的怪異崇拜,乃是源於千年科舉制度的遺風。雖然饒氏沒有狀元的冠冕,但最高元首習近平悼念其死亡,被人們引以爲人生中莫大的榮耀。宋代理學家張載曾有所謂“橫渠四句”,認為讀書人要“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其實不過是儒生書齋中的意淫。饒氏或許做到了“為往聖繼絕學”——然而,若這種“絕學”不能增進人類的自由和幸福,它不過是某種最低層次的“考古學”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