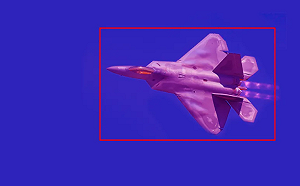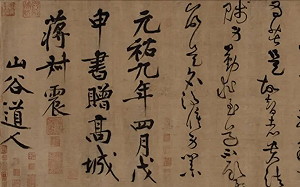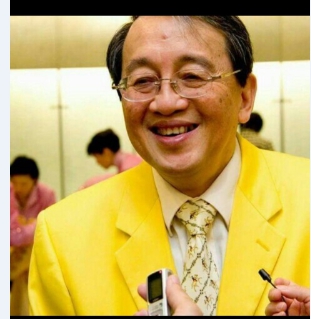這場對談很有意思,從發生到進行到結束,似乎就如「革命」般,充滿不確定因素。找廖偉棠(人在義大利)跟張鐵志(人在台北)談切‧格瓦拉,是因為這二位作家的特質相當迷人,而且對切都有深入的理解,某種相同的質素將這三個心靈互相拉扯住,在網路上以mail進行對話。編輯負責搖旗吶喊,發出mail提出第一個問題暖場:「第一次知道切是在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初次的印象如何?」(台北時間PM 04:28)為了真實的呈現,我們把時間也標示出來,這是非常即時的反應,打字速度先不說,要能夠在這樣的時間內寫出如此深刻的話語,不禁讓身為旁觀者編輯的我大為驚嘆!只有切有這麼大的魅力吧,他所影響的一代一代人,將他的信念繼續燃燒、延伸。(印刻文學雜誌編者)
廖偉棠(以下簡稱廖):可能很早就在某些影像上看到切的頭像,但不知道是什麼,還有在美國樂團「憤怒反抗機器」(Rage Against the Machine)的專輯上也見到過。但真正認識到切,是在一九九七年,我從香港到廣州買書,回來的巴士上我在最新一期《讀書》雜誌上看到大陸的拉美研究學者索颯寫的關於切的紀念文章,當時我在巴士上讀得淚流滿面,沒想到當代還有這麼偉大、無私的人。回到香港,馬上買到大塊出版的《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看了,很快又買到香港一家托派出版社在七十年代出版的《古巴革命戰爭回憶錄》,以及大陸七○年代出版的蘇聯人寫的切的傳記,於是對切有了基本的瞭解。對他的初次印象就是:那是一個可以信任、可堪追隨的人。(台北時間PM 04:36)
張鐵志(以下簡稱張):我記得,應該是九○年代前期的大學時期讀到格瓦拉。彼時終日投身於學生運動,搞讀書會、上街頭、在學校發傳單,手持麥克風在少少的人群前演講。除了專注於當下的台灣社會矛盾,我也很著迷歷史上的青年革命,不論是台灣從日治時期開始的學生運動,或者六○年代的全球學生反抗。然後,不記得在什麼書上,讀到了切的故事。那樣典型的革命者的故事,決絕的姿態。結合了勇氣與悲劇,獻身與犧牲。在那個我們正急切於尋找反抗典範的過程中,他當然是成為無可取代的典型。(台北時間PM 04:54)
廖:你提到勇氣和悲劇、獻身與犧牲,我想這是吸引我們的最初動機,其實這幾種特質在宗教殉教的聖徒(比如說聖塞巴斯蒂安)身上都具有,我們早年對革命的嚮往中也是混雜著宗教情感的。而你提到的決絕才是我們更進一步認識切的道路,他有別於其他共產主義當權者的一點是他對自身也非常決絕,具有苦修精神──當然這又讓人想到宗教,如聖方濟各(San Francesco,1182-1226)。但同時他對普遍的人類情感並不冷酷,他的革命是飽含了愛、愛恨分明的革命,如果只有愛不講恨那就和宗教無異,只講恨不講愛──那是極端左派如日本聯合赤軍那樣的。切是一個心懷大愛的戰士,他身上也有很多屬於人類的弱點,正是這樣的一個人才不至於淪為神話符號吧。如沒記錯,我是在他的《論游擊戰》的序上讀到他談論革命中的「愛」的見解的,深為折服,你看到過嗎?(台北時間PM 05:09)
張:你說的真好,且我正好在思考這一點。關於革命與愛。
我在我的書《反叛的凝視》寫切的文章時,引用了他的一句話:「一個真實的革命者是被偉大的愛所指引」。誠如你說的,他的革命是愛恨分明的革命。但我想,應該是以愛,對於被壓迫者的愛,對正義、和平的價值的愛為底蘊,然後才會出現對那些壓迫與支配者的恨。所以愛是指引。
回首歷史,太多的革命者以正義之名,但最後都是以醜惡的面孔出現。尤其作為一個革命者,是處在高密度思想和肉體鬥爭的處境,他的愛與善很難在與惡的鬥爭過程中不被一步步侵蝕。於是,許多革命者最初對人民的愛,很容易後來只淪為對權力的愛。
這就是格瓦拉最吸引人的部分。我在想,或許因為他是醫生,所以可以保持那樣的愛,如同我們在《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和《玻利維亞日記》中所看到的,對同胞與同志的愛。
格瓦拉還有什麼特質吸引你呢?
或者說,他對你相信的信念來說,還有什麼樣的意義呢?(台北時間PM 05:18)
廖:對,我在《論游擊戰》序言中注意到的也正是這句:「一個真實的革命者是被偉大的愛所指引」。很多革命者(在當代也存在這樣的人)在鬥爭中,很容易忘記了最初的革命動機,而對權力和榮譽的迷戀導致出一種變態的潔癖——認為其他所有人都不如自己革命,繼而以此為藉口來清洗革命隊伍,把恨放諸那些應該去愛的人身上,這些人也許是不夠自己「革命」的同志,也許是「革命覺悟」不高的人民,但無論如何,他們不應成為恨的對象。
切能避開這一點,除了因為他是個醫生,更因為他是個詩人──我是這樣理解的。他身上的詩人氣質,他的憂鬱都是吸引我的,也許他寫的詩滿一般的,但他的行為本身就是一首詩。至於說到他現在對我的意義,我和他不同的地方是我比他虛無一些,但正是他不斷提醒我在理想主義行為中存在的積極意義,讓我從不對理想主義絕望。他的行為告訴我們,那些被譏為空想的行為,竟然是可以實行的。他令我堅持了行動主義的信念,革命絕對應該坐言起行。
但畢竟不是全世界都是當年的古巴或今天的查巴達,那麼我們如何行動下去?我想聽聽你對切的鬥爭方式的理解,還有你覺得如何轉化為我們現今在城市中的鬥爭?(台北時間PM 05:35)
張:哈哈,你果然是詩人之眼讀到了切的詩意。是的,他的行動就是一首詩,抒情而飽滿意義。
回答你的問題。我覺得切的游擊鬥爭有幾層啟示:
第一、他對社會不平等、對弱勢的關切是這個時代最迫切的問題。當然,在資本主義體制中,這個階級矛盾的問題從來沒有消失。只是,隨著過去二、三十年的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國與國之間,以及一國之內的社會不平等增加了,且非洲大陸、南亞等地區人民的貧窮並未改變。改造資本主義的迫切從來沒有一刻停止過。而且,這個鬥爭不是正在進行嗎?從一九九九年西雅圖反WTO的抗爭,左翼、環保主義、青年安那其們,他們許多人身上穿著切的T-shirt,秉持著他的火炬,用身體去抵擋新自由主義的暴力巨輪。(那一年在香港,你不是也在抗爭現場嗎?我想起你那首我摯愛的〈灣仔情歌〉)
而這些格瓦拉的子民們某程度上是取得成就的:血汗工廠減少了,世界貿易談判的議程轉變了(更強調第三世界的發展,雖然還在談判中),公平貿易的概念越來越深入人心。然後,去年,新自由主義的資本邏輯吞噬了自己,造成內爆。當然,鬥爭還是要繼續。
第二,他的游擊戰對我們來說,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理解,亦即文化的游擊戰。面對資本主義的強大力量,除了與其正面對抗,除了用街頭的公民不服從取代切的山中武裝游擊,也有必要展開文化的游擊戰。透過各種文化的形式,音樂、詩歌、劇場等,去暴露體制的暴力與壓迫,去展現抵抗的可能。
我其實在想,切如此愛寫日記,他一定是很重視文字所能展現的力量。
你說呢?切對於你的文化行動主義有產生影響嗎?(台北時間PM 06:00)
廖:切對文字力量的注重這點你發現得好。其實他很敏感與現代鬥爭的新形式,比如當法國人德布雷被捕後,切並不感到害怕,反而高興於這樣一來會有傳媒、繼而是大眾知道和關注游擊隊的存在;而之前他在非洲給周恩來寫信要求支援大功率的發射電台,也是出於同樣考慮。如果切身處如今這網絡時代,他將會和馬可仕一樣如魚得水。我想這也是他對我們現在的文化行動的啟發,盡可能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傳播資源,把要求變革的思想傳達到任何可能、渴望接觸它的人眼中。所以我毫不避諱在社會運動中寫作和朗誦、傳播詩歌,我始終認為詩歌是可以有實際影響力和提供反思能力的(當然我也認為沒有上述兩者的詩歌也可以是好詩歌)。切的信念是能影響一個人就是一個,所以他在臨刑前夕還會對士官們「說教」。我的詩歌觀也如是,正如我曾經在一個訪談裡說的:詩歌對現實是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無能為力,但我偏就不放棄那百分之零點一,我的憤怒只對我的良知負責,如果有人傾聽或和應的話,就能賺一個是一個。
你對切的文字和著作最感興趣的是哪本?我最喜歡的,還是《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但最震撼我的是《玻利維亞日記》,我以它為藍本寫了一部詩劇《玻利維亞地獄記》。(台北時間PM 06:20)
張:和你一樣,最喜歡《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主要還是因為相對於其他幾本書,是比較細瑣地談游擊戰過程,摩托車日記更有血肉,有對土地傷痕、人民苦難的描寫,也讓我們看到一個青年理想主義者的成形,讀到那些青春的純粹熱情。
你對詩的看法也正如我對音樂的看法,我深信音樂或其他文化形式的力量,對人們意識的衝擊與塑造的力量。所以我特別有興趣於文化和社會運動的接合。兩者都是在抵抗。文化創作是要抵抗既有的價值、意識形態與霸權,是要創造另一種想像可能。社會運動則是改造壓迫性的政經、社會結構。兩條路線的行動者可能是分開的,但當他們結合時,就會產生巨大的力量。當然,我這幾年都是在以搖滾作為文化的切入,去挖掘搖滾的激進主義及其限制。
我也是這樣期待自己的文字:希望文字書寫成為我的文化實踐之一。我寫的題材乍看比較雜,但其實都是一貫的:去揭露、批判資本主義或威權政治的壓迫,或者比較抒情地去書寫那些反抗行動,不論是搖滾人的社會介入,或是如《反叛的凝視》一書中所討論的各種行動者,這是因為我自己被他們深深感動或是inspired。
當然,文字,或者文化行動,還是必須植基於書房外的行動中,這樣的文化實踐才是有機的,也才能讓我們不斷地反省文化實踐的可能虛弱,起碼我是常常覺得自己的不足。(台北時間PM 06:38)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