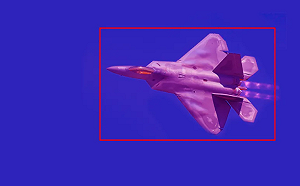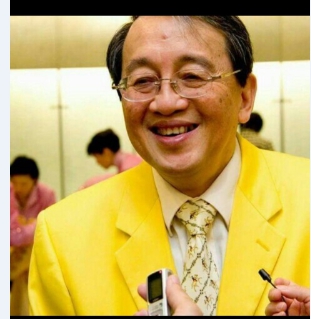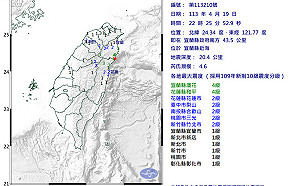車子抵達新加坡Raffles酒店門口,一位服務生隨即趨前幫我拉開車門(另一位則幫我從車箱取出行李),並引領我進入Lobby的沙發座椅,問我要不要來一杯Singapore Sling還是其它飲料?
當然。來到Singapore Sling的發源地、住在名聞世界Long Bar的酒店,怎可不喝這杯響噹噹的Cocktail。
就在等飲料與等辦Check-in手續的同時,我才注意到我所坐的地方是酒店傳奇的Writer's Bar;Lobby另一側是Tiffin Room,竟日提供餐點與喝下午茶的餐廳。幾乎所有初抵的住客,都被安排在Lobby兩側的沙發座小歇。亮麗的陽光穿過挑高3層樓上方的玻璃,灑在Lobby正中央那碩大的盆景,紅花綠葉散發出熱帶的鮮艷與Lobby內側深黯木質樓梯流露的歲月痕跡形成強烈的對比,予人一種充滿東方、帶些慵懶的浪漫;幾乎所有的客人莫不被此景所吸引,隨即拿出手機猛拍Lobby的每個角落。我猜想這是酒店「有意」的巧妙安排,讓服務生引領客人坐在Lobby兩側沙發椅等辦入住手續、喝Singapore Sling,把腳步放慢、心情放緩,欣賞它從1887年所流下來的風華與魅力。
新加坡Raffles是亞洲少數幾家建於19世紀至今還在營運的大飯店,它已成為新家坡的地標,住客名單就等於另類名人錄;英國名作家Noёl Coward、Somerset Maugham、Rudyard Kipling等人曾住在此旅館寫作,為了紀念這些文人雅士,而有Writer's Bar。這幾位作家當年到東方來也曾入住曼谷The Oriental酒店,因此該酒店把早年那棟多位作家住過的建築冠上Writer Wing(作家廂房);曼谷The Oriental酒店成立於1876年,也被歸為亞洲19世紀的大飯店,幾年前我入住時,總經理特別陪我參觀Writer Wing聊一些陳年逸事。
Writer's Bar(作家酒吧)是一個小酒吧,它也是Raffles Grill餐廳的一部分,就在這家餐廳的門口。歐美的餐廳通常會設有Bar台,提供客人餐前喝個開胃酒或餐後喝餐後酒、咖啡聊天,縱使不是用餐的客人喝杯酒水也常有所見。Grill是一家優雅的現代法國餐廳,木質地板、幽黑晶亮的木質座椅,簍空雕飾的椅背,黃銅發亮的枝型吊燈與垂吊的風扇,再再流露它的典雅,透過落地格子窗往外看就是酒店的Palm Court(棕櫚庭),一大片修飾整齊的翠綠色草地與棕櫚樹。而Writer's Bar的Bar台才只有4個位置,其它就是沙發座椅與小圓桌。我雖只住個三天兩夜,但卻常在此喝酒;Bartender Ben知道我來自台灣,他告訴我他的母親曾在台北幫傭一段時間,他則從未來到台北。
Raffles酒店的地址是Beach路1號,它位在Beach路與Bras Basah路這兩條路的交會口;此趟新加坡之行,我與曾擔任台北亞都酒店的法籍總經理Andre A. Joulian夫婦住在Raffles,他告訴我,三、四十年前他曾經到過此酒店,當年酒店臨近海邊與沼澤,地址Beach(海灘)路因此而來,如今這一帶填海造陸起高樓,也看不到大海。今日酒店的某些房間與精品店則在Bras Basah路這側,每家店等於有兩個店面,非房客則從Bras Basah路進入、房客可從酒店內側進出這些精品店,為預防非酒店住客進入住客的房間,除了有鐵柵欄區隔之外(但不會讓人有突兀之感),只有住客使用的鑰匙才能上下電梯。
酒店傳奇的Long Bar則位在Bras Basah路這側,走在狹長的騎樓,遠遠可以看到一個墨綠色底印有Long Bar與箭頭的招牌,Bar在二樓,階梯用粉紅色畫出一杯立體的Singapore Sling面對著過路客。踩著木頭階梯拾級而上,牆壁與二樓的入口處,都用畫作與英文細數Singapore Sling的點點滴滴。

Singapore Sling不只與Raffles劃上等號,它也是新加坡的象徵。1915年Long Bar這位來自中國海南島的Bartender嚴崇文,用英國人習慣的Gin為基酒,再調混櫻桃口味的白蘭地、Cointreau(一種法國甜橙酒)、鳳梨汁、新鮮檸檬汁等等調成這杯粉紅色澤的Cocktail。去年是Singapore Sling問世百年,酒店通往Long Bar的庭園沿途用立牌敘述這杯酒的故事。
如同Long Bar這名字,其特色就是有一條約有十來個座位的桃花心木Bar台,至今仍呈現深沉卻也帶著亮麗的咖啡色澤;在Long Bar可以把花生殼隨意丟到磁磚鋪成的地面上。試想,當年那些重視著裝規矩的歐洲人,在此喝著帶有熱帶風味、口感微甜冰涼的Cocktail,一定充滿異國風情的感受;又可以放肆隨意丟花生殼,踩在腳下發出的迸裂聲交會著酒客高談闊論聲,他們在此一定有從歐洲獲得解放之感。今日,在新加坡有很多的「不可以」,Long Bar是唯一允許可以把垃圾丟到地面的地方,仍可享受「不必守法」的快感。
從Long Bar下樓拐個彎就是Cad's Alley,走過這不到十步的通道就來到Raffles的庭院餐廳Courtyard,它是一個相當廣大、輕鬆自在的露天用餐區,Courtyard兩端各有一座磁磚做成的大Bar台。
Long Bar適合觀光客與朝聖者,該酒店歷史最悠久也具有典故的Bar and Billiard Room(酒吧與彈子房)反而被忽略了;晚宴後Joulian與我及其它幾位朋友繼續在這個Bar喝酒聊到深夜,他說他最喜歡這個Bar。我很認同他的看法。
約一個小學禮堂大的Bar and Billiard Room,Bar台就在正中央,高腳桌椅、長方桌與沙發椅、方桌與藤椅等等位置錯落在Bar台的四周圍,一張年代久遠的撞球台則在一個牆角,枝型吊燈從高高的天花板垂吊而下,吊扇慢慢轉動、昏黃溫柔的燈光讓人感受時光的倒流;室外暗紅地磚的長廊,也散置著桌椅,似乎在那邊存在已久。看到此景,突然讓我想起1960年代初期我就讀省立嘉義中學在學校附近的那些簡陋彈子房。
沒有錯,Bar and Billiard Room是新加坡現存最老的一家Bar,這個建物於1896年就獨立存在;它就緊臨著酒店的走廊與Tiffin Room餐廳,目前已建了一個通道將兩個建築體銜接在一起。剛成立的時候有5張撞球台,目前僅存一張,但仍可使用。這個Bar有400多種Whisky,一個靠牆的酒櫃就陳列著蘇格蘭、美日等國上百種品牌的Whisky。
在歐美許多悠久歷史的大酒店,Bartender清一色都是男性,但Bar and Billiard Room在1920年代第一家聘用女性當Bartender,造成騷動。不過我喝酒的那晚Bartender是男性。讓我想起當年在嘉中附近的彈子房,很多人為計分小姐爭風吃醋,打架鬧事常有所聞。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