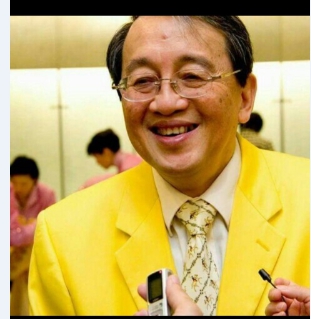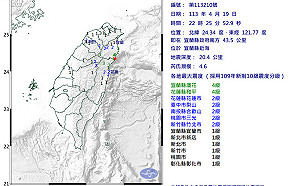[前情提要]
到每班去演了「看不見的炸彈(反核繪本)」走遍全校,另編劇本參加鎮上的「環保劇展」得了首獎,用獎金辦了文史之旅回來又「出版」了「旅行小書」…小文的班級簡直紅透半邊天了,走到哪裡都得到人們的誇讚;然而,在我們的教育體制裡,這樣的老師,用這樣的方法帶班,帶出這樣的班,嗯,事情似乎不該總是這麼順利:於是,到了四年級下學期,他們終於要踼到鐵板了。

(圖:翻攝自森林小學網站)
獨立公民報
每年5月,學校都要辦理「自治幹部」的選舉;而四年級,正好可以選「環保小局長」。老師們都知道反正學校又不會真的讓小孩「自治」,所以這場選舉,也不過就是小孩和家長們的一種「愛現的活動」罷了;但小文老師已經把她的班級帶成這樣,怎麼可能讓這些小孩相信,有些事情是不必當真的呢?
小文沒辦法,只好眼睜睜地看著他們開班會,認真討論「是先推代表,還是先擬政見」;一面心中暗想,不知道這些孩子是選不上比較失望,還是選上了發現真象才更失望?但他們已定出了好幾個政見,而且決定先在班上試行3個禮拜,看看哪些真的可行,哪些只是說著好聽。
終於,離投票只剩2週了;公認最能言善道的傢伙被派去登記參選,但看起來,這整個班級才是候選人。為什麼呢?因為所有的競選活動,根本都是全班出動。之所以要動用那麼多人力,也有一個原因,因為他們為了「環保」的原故,決定從頭到尾只能用一張海報來宣傳,其它任何道具都不行,連名片都不能撒;這麼一來,只好用人海戰術了:利用下課或早中午的任何時間,3個人一組,到校園的各個角落,向別人介紹他們的候選人,但又強調重點不是「人」,而是他的政見…
當然,這裡面絕對有「反核劇」所留下的影響,那時候,他們曾經廣泛受到各班的歡迎;但競選是另一回事,作用其間的,絕不會只有一股力量。小文老師心裡替他們著急,但又無法反對他們的「純潔」與「純情」:別班的候選人,無不極盡所能做出各種道具,放在各個顯眼的地方,吸引所有人的眼睛;經過的時候,你會聽到小孩驚呼「哇,好可愛噢!」,或者「這要去哪裡買啊?」,或者「好特別噢,明天我們也要再加一樣…」,但幾乎沒有人注意到夾在道具中短短幾行的「政見」。這不能怪「選民」沒有眼光:所有的政見幾乎都一樣,無非就是「我們只有一個地球」之類的;於是,選民即使有眼光,也不知道要射向哪裡。至於小文他們班的那張寫滿了字的海報呢?人們會誤以為是誰貼的什麼公告吧?在繽紛熱鬧的「裝置」之間,沒幾個人想到這也和競選有關。
然而,情勢的不利還不止此:競選活動才開始,身兼活動組長的老師,就來制止小文班的宣傳,理由是:不能私辦政見發表會,這樣對其他候選人不公平;那麼,什麼時候才能發表政見呢?活動組長一時語塞,只好答應說:我會安排公辦政見會,到時候你們可以來講。所以,小文班至少有一個功勞,就是逼出一場公辦政見會;問題是,那已經是投票的前一日了,而且每個候選人只有10分鐘的時間,而且,又有誰真的會去聽或聽得進去呢?
總之,結果是不用開票也就知道的,只有小文班不知道,還以為只有他們才有資格當選:其他人連競選的時候就已經不環保了,還選什麼「環保小局長」?落選的消息傳來,全班群情激憤;尤其是聽說勝選者所有的道具和政見都是媽媽做的,而且這位媽媽還是學校的一位老師。看著這些眼中含淚的小孩,小文老師不知道怎麼安慰他們;她尤其不敢跟他們說,過去的成功只是僥倖,現在的失敗才是常態:這個世界從來不如我們希望的那樣合理,而任何的「理想」都是要經過一再的奮鬥還未必能實現…
做為一位老師,她本來是有一句現成的話就在口邊:沒有關係的,你們已經盡力了;然而,小文並不是普通的老師,她深深地知道,對這群孩子這樣說,會是一種侮辱:他們並不是只在意結果,他們更在乎的是導致這個結果的那種荒謬︱不是說民主是最高的價值嗎?不是說都應該讓民意決定嗎?可是,可是民意怎麼會這麼糊塗!
然後,她就聽到有小孩說「以後再也不做這種事了」,「別人都不環保,只有我們環保有什麼用」,而越來越多的小孩附和「下課時間就應該玩遊戲」。小文老師不能制止小孩這樣想,因為,在他們身上她清楚地看到自己,看到自己這些年來的心路歷程:每次都以為公道自在人心,但人心從來沒有那麼公道,不止一次地,她都覺得「不如算了,何必那麼辛苦?」
過了不知多久,小文老師才開口:「我提一個問題,你們大家想想看;如果今天是我們當選了,那些沒選上的人會做什麼?」一時之間,小孩有點轉不過來:什麼「我們當選」?明明就是我們選輸了啊!但過了不久,就有人說「我們也可以幫助他」;接著又有人說「告訴他應該怎麼做」,「告訴他不該做什麼」…當然,還是有人潑冷水:「幹嗎多管閒事」;不過,看起來,整個的氣氛已經慢慢緩過來了。
小文老師於是說:還記得之前我給你們看過的「公民新聞報(公視的節目,播出公民記者製作的新聞)」嗎?還記得那時候我們說過媒體應該「獨立」才能監督政府嗎?所以,我們既然選輸了,就應該監督選贏的人…說來奇怪,這「監督」兩個字,好像有一種魔力,班上的主流意見忽然就轉了一百八十度!
不知不覺走到這一步
早就放學了,辦公室只剩下自己一人;身後忽然傳來:「獨立公民報?這又是你們班的新花樣?」小文抬起頭來,對阿建老師說:對啊,我這個小編總得幫忙修修文句,調整排版嘛!阿建彎下身細看,頭版頭條居然是「不環保的環保小局長」,而小文正在把它改成「環保小局長的選舉問題」;其它各版的文章可就多了,什麼「礁溪溫泉問題」,「校園蟑螂問題」,「小蓉遭遇的問題」,「鐵路東移問題」,「體育班的問題」…最有趣的是,還有一篇是「我班小文的問題」!
當然,每篇的文字都不會太多,而且還都配的有圖,除了小作者的手筆外偶爾也夾的有照片;總之是琳瑯滿目,攤滿了好幾張桌子。阿建老師看得眼都花了,忘了原本回來是要做什麼;不知不覺在旁邊坐下,忍不住提出心中長久的疑問:你到底是怎麼變成這樣的?小文聽不懂:變成怎樣?阿建說:就是變成這樣的老師啊?小文定定地看著他:你真的想知道?這要講很久耶!阿建微微地笑了:難得辦公室空空的,我們可以從這頭講到那一頭。
小文說:起頭就是大一的時候無意之間參加了「生態保育社」,沒料到一下子就涉入反核,反濱南工業區(包括七輕石化),反美濃水庫;才發現和同伴一起反對不公不義,讓我心裡極為快意︱中學之前我都是乖乖牌的好學生噢!大三的時候,接觸台灣文學,開始體會大時代下小人物被壓迫的處境;當然,也包括在各大國之間,台灣的孤兒般的歷史。大五實習的時候,參加了「台灣教師營」,第一次看見真正的「老師的樣子」;這些老師和我們平常看到的非常不一樣,他們關心國家大事,盼望著台灣的獨立︱我也想要成為這樣的老師!
阿建靜靜地聽著,不插一句話;小文喘了口氣,接著說:但一開始當老師的情況,你一定想像得到,簡直是一塌糊塗;直到教書的第4年,我去參加了民間團體辦的「正面管教教師營」。那一年,恰好第一屆的孩子(也就是孟豪那一班)辦同學會,我就去正式地向他們道歉,說「那時候我會打人,表面上是為你們好,實際上是不知道怎麼教…」;接下來我每年都參加「教師營」,除了思考帶班的問題,也追求更好的教學的方法︱大家都看到我在帶小孩參與社會議題,其實我花更多的時間備課:國語課一定要讓小孩思考除了寫出來的文字之外,作者還想表達什麼,或特別不想涉及什麼;數學課一定要讓小孩進入實際的情境,要有感覺,絕對不能只是計算題目…不過這部份沒那麼容易,我還在繼續努力!
一口氣講到這裡,也差不多講完了;好像也沒講多久嘛,小文心想,一面問:那還要講什麼呢?阿建還只是微微笑著;小文只好接著說:「教師營」的老師曾說過,我們自己應該不斷地追求一種「愛智的生活」,教學並不能只是一種帶小孩的工作;嗯,我最近正在看「阿德勒」的「被討厭的勇氣」(日本作家根據阿氏的理論所寫)…
聽到這個書名,阿建老師突然說話了:其實我們好幾個老師都對你很好奇,本來只是好奇你的「勇氣」,現在更好奇你是怎樣在努力;因為,套你的話說,就是︱阿建有點猶豫,但還是說了出來:就是,我們也想成為這樣的老師!
尾聲
「我們也想成為這樣的老師」!小文的心中,突然閃過一道亮光:這麼多年以來,我把全付心力都放在小孩身上;從來沒有想過,我也可以更用心地去影響其他的老師,正如,正如深深影響了我的那些老師一樣!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