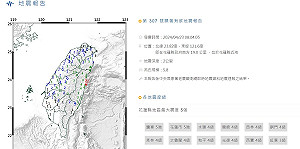每天從住家抬頭一望,Shangri-la台北遠東國際酒店那兩棟現代化的高樓就聳立在我的眼前;走到巷口,台北地標101大樓更有如高高在上的君王,日夜鄙視著賤民的我。相較於我所窩居的六張犁社區以及周遭的環境,我常有茍活於貧民窟之感,總想起墨西哥人的遺憾:上帝,我離您那麼近,卻離美國那麼遠。
特別是,當我從Mandarin Oriental的MO Bar喝完酒搭上285、902、556公車回家,車子從敦化南路寬敞的林蔭大道左轉狹窄的和平東路,再經過基隆路,可說是不同的兩個世界;或者下班路過Shangri-la酒店在一樓的Gin Bar喝完Martini後出來,安和路的景觀也有別於我要回去的六張犁住家。結帳時,我偶而跟Bartender開玩笑,知道Cinderella(仙履奇緣)的故事嗎,總得要回到現實。六張犁雖屬人人稱羨的大安區,但要看那條路的大安區,仁愛路、信義路也都屬大安區,而在我眼中和平東路就差一截;還有那個路段的大安區,而基隆路就是一個分水嶺。不信的話,比比兩旁的景觀就一分高下。
我住的這棟五層樓老公寓,樓下是木頭門,門兩側是住戶的木板信箱與門牌號碼,但多數信箱的門都已斷落,因此看不出門牌號碼;由於此區多雨潮濕(特別是梅雨季,我打傘出門,到大安捷運站,地面是乾的。)一二樓的樓梯旁的白色牆面,縱使重新粉刷,但不久又剝落不堪。
住家附近都是四、五層的老式建物,平均一至二個月就聽到其它住家敲敲打打,那些鑽樓板的聲音更常叫人發狂,而且從後陽台下的防火巷產生共鳴,似乎就敲打在你的頭頂;特別是春節前那一兩個月,有時會同時幾戶在修繕,那真是人間地獄。正面樓下的巷弄,全部早已成為一樓住戶私畫的停車位,尚可容一部車通行;後陽台與另一棟的後陽台距離雖不至於「屁股對屁股」,但從罵孩子到貓兒叫春或貓在遮陽板追逐的跳動聲,或那個鄰人歇斯底里的哭聲與無理頭的叫罵聲,或年輕人週末夜的狂叫嘻笑聲,半夜洗衣機的低沉卻不是安眠的攪動聲,汽車或摩托車半夜返家的引擎聲等等你可以想到的噪音都存在,對了,我還沒提到上午9點多偶而有更動人叫床的呻吟聲(我通常10點後出門打工)。這不是貧民窟,什麼叫貧民窟。更無法忍受的,一年到頭總有住戶焚香燒紙錢的,我雖住4樓,但那些叫人喘不過氣的異味有時連晚間都還餘煙裊繞(二樓住戶,似乎焚香不斷,樓梯間門口的白色牆壁都被燻黃)。
有時,選鄰居比住那個區重要,改天若有人告訴你「他(她)住大安區」,也不用太羨慕,看看住家附近的環境更重要。
週六假日陪老媽吃完午飯、看完「蠟筆小新」,一點以後,我會到樓下斜對面的Subway喝杯咖啡,看小說或The New Yorker,或改學生「新聞採訪寫作」的作業。它有18個座位,約一般Subway的大小,但我不會占到其它用餐人的位置。
通常固定有兩位中年婦女招呼客人,其中一位英文流利(我猜想她是老板),另一位我則沒有聽她說英文,有時後者這位沒有當班,會有另一位中年婦女招呼客人,她的英文更流利悅耳。每次幫我做咖啡,都是那位「我猜想她是老板」的婦女,幾次後,只要我進店,她就為我做黑咖啡,而且杯子不用加蓋。我們除了「謝謝妳」、「再見」,沒什麼交談。
這兩三年下來,自認住在六張犁「貧民窟」的我,發現這一帶的「老外」似乎變多了;我大約停留1個小時,少說總有三四個老外進出,有的外帶、有在店內用餐,從老板與他們英文會話的內容,我想他(她)們都是住附近的老外,說英文居多,也有說西班牙、德語的,甚至我聽不懂的(或許是來自東歐,白皙的皮膚、金髮、姣美的身段)。
與2005年之前的天母「老外」相比,當年那批大多數為白領、甚至是主管階級的「老外」,如今已不見,天母早已不是相對高消費的「洋人區」;而與我同住在六張犁的「老外」,大多為年輕人,他(她)們或許共同在此租屋同住。
每當我走在紐約Soho、TriBeCa、Nolita這些老舊的Neighbourhood,看到無數用紅磚或石塊蓋的老房子,無論是店面或餐廳總叫人留連忘返,而台北,甚至台灣各地除了路邊攤,還是路邊攤,不僅沒有個性,也失去它的優雅。
不知六張犁社區有沒有機會創造自己的風格,而不只想到都更與炒地皮。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