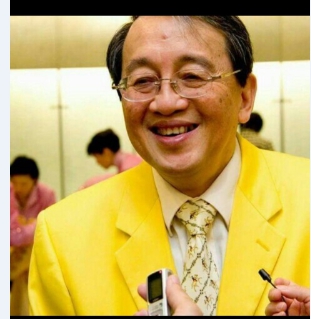網上筆談兩小時倏乎而過,一點也不冷場,竟比看動作電影還刺激。幾乎一字不改的原文刊載,除了發現作家的思路脈絡,也可見文字比言說似乎多了一層清澈的質感,直入人心。可畢竟是打字,兩個鐘頭共合寫了約三千二百字,已經是驚人。意猶未盡之餘(寫的人跟即時監看的編輯都是),遂相約隔日同一時間再戰兩小時。(編者)
廖:午安!鐵志、逸君。我們繼續我們的游擊吧。鐵志你終於看到足本的電影《切‧格瓦拉》上下集了嗎?我是上個月在香港電影節上看的,當我看到下集切‧格瓦拉的遊擊隊在猶羅峽谷中最後一戰時,耳邊是淒慘得如來自另一世界的零星鳥啼、加上那一兩個長度不超過十秒的主觀蹣跚的鏡頭,一下子糾結起前面三個多小時的壓抑,轉換成泰山欲傾的巨力向我壓下來。那一刻我突然感到渾身戰慄,不覺間竟然淚流滿面——那完全是他一個人求索的地獄,我覺得Steven Soderbergh對《玻利維亞日記》裡那種彷彿被命運控制的氣氛理解得很好,成功轉換為影像,他用目不暇給的鏡頭切換配合明亮環境下的淺景深,成功地營造出游擊戰中充滿不可知因素的噩夢氛圍,我們不時看到焦點外的世界如幽靈一樣向鏡頭飄來,迅即又落回實處,這種一張一弛的節奏也像極了切在《玻利維亞日記》裡記載的戰爭,還有隱藏得更深的切‧格瓦拉的內心:孤絕的意志在痛苦中咬牙、衝突。
這部電影不迴避殘酷,我覺得比《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拍得好,《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把現實的矛盾簡單化和淡化了,變成了一部青春成長小說式的電影,過於突出溫情和夢幻,而忽略了現實是夢魘。
我在那部電影中感受最痛苦的是:那出賣游擊隊的農民羅哈斯臉上現出的一個最平凡、最正常的、人的表情,這一張臉,和不久面對死亡的切‧格瓦拉的那一張臉,竟然都屬於人類之臉。人究竟是怎樣的一種動物,是否還存在救贖的可能?我們面對背叛和不理解的時候,都忍不住自問,我們為之付出的努力是否有意義?但切更無私,超越了這種質疑,他完全相信意義就存在於尋找意義的行為本身之中。
張:我還沒有機會看到Soderbergh這部片,但我知道台灣在這個夏天會上演,很期待。
電影作為一種大眾文化的力量,確實影響力深遠,我可以想像,這部片在台灣上演時,必然又會捲起一股格瓦拉熱潮。但這也正觸及了我們這個時代的格瓦拉現象的核心矛盾:切的商業化,以及革命的庸俗化。
我們該如何看待他無所不在的頭像,尤其是各種商品上的英挺頭像?而這部新的電影除了讓我們對切有如
你所論及的理解外,可以讓新世代更理解切真正代表的革命精神嗎?
切的商品化在現象古巴也一樣。我前兩年去哈瓦那時,就發現切已經是他們最大觀光商品,氾濫到讓人幾乎都不想買。如果我們對於卡斯楚的矛盾情結是,他是一個後來成為政治獨裁者的革命者;對於格瓦拉的矛盾情結則是,他是一個後來成為商品化偶像的革命者。
不過,某方面來說,我對於這個現象倒不是完全批判。因為人們總是需要令人感動的故事與啟發。切成為一個大眾的英雄並不是壞事。畢竟,如我前面所說的,還是有許多對全球化的反抗青年把切的頭像穿在身上。他們並沒有忘記切的真正精神。而且,還好他的形象不是屬於某企業的智慧財產權,而是可以被不斷複製、再造。你可以在任何國家的地攤、夜市看到。這不也是一種對當前資本主義私有財產邏輯的顛覆?
當然,更重要的是,我們如何去介入對於切的詮釋權,如何讓他成為不只是商業機器的搖錢樹,而是在他已然被大眾化、流行化的既有事實下,去讓那些只以為這個頭像很酷的年輕人,對於切,對於左翼歷史,對於切的精神在現實的實踐,有更多的理解。
廖:這點我和你觀點很接近,不吐不快,所以剛才我已經也在同時寫,剛剛寫好就看到你的信,真是一拍即合!
切的影像和事跡的傳播,的確有被流行商業文化利用的嫌疑。但是反過來說,也可以是切的幽靈對商業傳播的利用,我常這樣說:假如一千個人因為迷戀切的頭像之帥和酷而購買相關的產品,其中或許有十個人對這個帥哥頭像背後的思想產生好奇,然後去尋找關於他的文字、去了解他的意義;而其中有一個人被他觸動、感召,繼而想行動起來做點什麼去改變這個需要變革的世界,那麼這被利用也是值得的。
我看過紀錄片《暗殺卡斯楚的638種方法》,當被問及為什麼不怕暗殺的時候,卡斯楚說:「我有道德防彈衣!」而在一九九七年紀念切的遺骸運回古巴時,卡斯楚的講話中說:「我也把切當成道德力與日倍增的巨人,他的形象、力量與影響澤被全世界。」道德正義正是切無敵的武器,卡斯楚用之武裝著自己也武裝了古巴,即使他在一次次的講話中也有利用切的偶像號召力之嫌,但是毫無疑問他也幫助切‧格瓦拉實現了一個理想:讓殉道者的精神成為抗爭者的意志、動力。他一九六七年、六八年大量「輸出」切的影像、開放切的著作的版權讓各國翻譯出版,這都是好事。所以我們看見當今世界各地的抗爭街頭上,飄揚的都是切‧格瓦拉的頭像作為旗幟,而不是來自好萊塢造夢工廠生產的任何一個英雄人物。
不過,切和卡斯楚相比,分野最大的還是切毫不戀棧權力;最近在美國的古巴流亡作家紛紛撰文批評切‧格瓦拉,說他在獨裁和對暴力的迷戀中不遜卡斯楚,我看了一些翻譯過來的文章,覺得極像是捏造的。你怎麼看?
張:很高興我們很有共識啊,而且總是你說的比我更清楚。
提到他和卡斯楚的比較,這是我一直以來對於社會主義革命的感想。
過去幾十年來,很多左派因為反美,反對美國對古巴禁運,所以高度支持古巴。但是我覺得,支持古巴人民,和支持古巴政權,是不同的。我們不能因為卡斯楚的反美帝,或是他在教育、醫療方面進步的社會政策,而對他的獨裁視而不見。一個人長久把持權力直到老死,這絕對不是一個進步左派可以接受的。盧森堡與列寧當年的辯論已經很清楚說明,社會主義不能沒有民主。
對於民主,說實話,我們不太知道切的細微立場。例如你提到那些文章,我們無從知道是否是捏造。切對於前朝官員的執刑,這是一個典型轉型正義的難題:該如何處理之前獨裁政權的官員?至於說他鎮壓異己,這個為了權威與紀律而鎮壓異議的問題,的確是革命行動普遍的內在問題,如日本赤軍連後來的發展,這是值得我們集體反省與思考的經驗。
切如此做,這主要是因為他把革命理念純粹化,而非為了鞏固自己的政治權力。事實上,切對於權力的立場是另一個他被人尊敬的原因。一九五九年後,他看到了當年同志的日益庸俗化、墮落,看到了革命終將被官僚體制邏輯吞噬並逐漸自我背叛化,所以他選擇了放棄權力,繼續上路去革命。
正如沙特和許多曾經支持卡斯楚的左派,對於卡斯楚的日益獨裁在一九七一年的公開批判信的最後所說的,「我們重申,我們與當時指引著山中游擊鬥爭的原則站在一起,而這個原則是卡斯楚和格瓦拉曾一再以言語和行動所展現出的。」
廖:所以我覺得要從兩方面看切的意義。第一,是他作為一個個人的意義,他以其對肉體疾病和權力誘惑(也是一種病)的超越,證明了一點:人是可以超越、並應該超越的,在物欲橫流的時代,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奇蹟。而同時他人性化的種種行為又反駁了聖徒化和革命樣板英雄化他的可能,他是一個悲劇英雄,又不止是一個悲劇英雄,他知道自己所面對的地獄,毋寧說:他是地獄的從容體驗者。第二,是他作為人民抗爭方式的一個轉折點式人物的意義,他身上有早期共產主義者如盧森堡的自律氣質和犧牲精神,但又有無政府主義者如巴庫寧、克魯泡特金等人的魔幻與樂觀主義(這點在他最後的歲月糾正了他剛掌管革命成果時可能的極端),這幾種精神如果結合起來,產生的是現今城市青年鬥爭所需要的素質,這是切作為一個行動者的演示。他的游擊戰思維更是適合當代,更何況我們有了更廣闊的游擊場域:網路。
張:此刻,那些不正義的壓迫制度,仍然強大,且全球資本更會流竄,並以更細緻、更多樣的面貌展現。
如今我們的游擊戰場或許不在山中,而是如你所說的,有更廣闊的戰鬥場域:網路。的確,尤其是相對於資本構築起來的主流媒體,網路提供我們文字與影像的游擊空間,尤其是對於中國這樣的威權機器,網路更是主要鬥爭場域。但另一方面,街頭的鬥爭依然重要(我突然想起滾石樂團的名曲Street Fighting Man)。就在我們對話的今日早晨,我和朋友們在凱達格蘭大道上被警察追逐,我們高喊著人權,要求國家把集會遊行自由還給人民。
當然,文字、思想、與街頭行動的各種抵抗形式,都是同樣重要。這就是格瓦拉之於我們的火矩吧。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