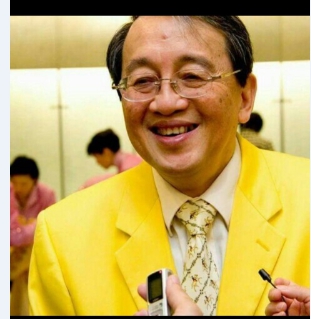巴黎Ritz酒店知名的Hemingway Bar的首席Bartender Colin Peter Field曾說過:「我總喜歡為作家調一杯Dry Martini,因為作家需要喝酒,一杯Dry Martini。」Hemingway Bar才只有34個位置,卻因為它以作家及其相關令人回憶的照片為裝飾而聞名。
我從1970年代在稿紙上「爬格子」到今日在電腦前「打字」,身為記者寫稿,不敢以作家自居,但始終愛喝Dry Martini,而且每次通常不會只有一杯。喝酒總悠遊於我的字裡行間,也像一條針線串起我的採訪、閱讀、寫作、旅遊時光,酸甜苦辣兼具。就如這杯苦中帶酸以The Journalist(記者)為名的Dry Martini(用Rutte dry gin、martini extra dry vermouth、martini rosso vermouth)。
記者出身後來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美國作家海明威,他本人與小說中的人物喝各種酒與他自創的Cocktails。海明威格外喜愛喝Martini,他認為Martini是「文明的風味」,他足跡所到之處,從巴黎到威尼斯、紐約、紐奧爾良、佛羅里達州Key West、古巴哈瓦那,甚至在非洲比利時剛果狩獵時所搭的小飛機墜機後他還是喝Gordon's Gin。海明威把Martini寫進他的小說裡也就不足為奇,在「戰地鐘聲」、「戰地春夢」、「伊甸園」、「激流中的島嶼」、「渡河入林」這些小說裡的人物也都喝Martini;甚至他與友人往來的書信也都提到Martini。
海明威在「流動的饗宴」這本文集記錄他在巴黎的歲月,他常去Ritz酒店喝酒。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海明威擔任美國知名雜誌Collier's的駐歐戰地記者,戰爭末期他比盟軍早一個小時「解放」巴黎Ritz酒店(1944年8月25日中午),在酒店裡靠近Cambon路這側當年並不知名的Le Petit Bar (Little Bar,小酒吧)喝起Perrier-Jouet香檳。Ritz酒店內有許多Bar,1994年為了紀念海明威「光復」Ritz酒店50週年,酒店指派首席Bartender Field將這個「小酒吧」改為今日充滿傳奇的Hemingway Bar。
擁有King of Cocktails(雞尾酒之王)美譽的Martinis是美好生活、奢華、世故的象徵,誠如美國作家H. L. Mencken(孟肯)為Martini下了一個最美的註解,稱Martini是美國唯一的發明有如十四行詩的完美。
每當黃昏時刻,不論我在紐約城中區東52街的The Four Seasons餐廳(與「四季酒店」無關)或The Bemelmans Bar(在Carlyle酒店)還是21 Club(西52街)這些以Martini聞名的Bar喝Martini的時候,我總想起E. B. White這位喝Martini出了名的The New Yorker(紐約客)名作家的名言,他說他喝Martini就像別人服阿斯匹靈,他每天中餐與晚餐都喝Martini直到80多歲(他得年86)。他認為Martini有一種無言的效果經常在他耳中響起,此時約下午5點,他所有的思維都趨於寧靜。紐約社交圈知名的高檔雜誌Gotham月刊在2012年有篇文章細數100年來紐約人喝Martini的點點滴滴,當然少不了The Four Seasons餐廳,這家餐廳與它的Martini是同樣的經典;而Martini也成為紐約的一部分。
回到台北這個不是喝Martini的社區,但卻有一處有四十多種Gin的台北Shangri-La一樓的Gin Bar,照例我請Bartender Emma(鍾)幫我做一杯Gin,這次她先將法國的Citadelle Réserve 2013冰到攝氏零度以下,倒入冰冷的雞尾酒杯,再低進幾滴義大利橄欖油。凜冽的口感趕走台北今年長久的濕熱。(Citadelle從08年推出在法國橡木桶陳年的Réserve Gin,釀出口感較為圓潤的Gin;13年這款改用材質較緊密的美國橡木桶陳年,而且首次使用釀製雪莉酒或西班牙白蘭地的Solera法,釀出口感更為緊密,香草、柑橘、杜松等香氣更為集中的Gin。酒架上還有G'vine Floraison(綠色系列)、Josephine這兩瓶法國Gin;餐飲營運經理David(王)建議我用白蘭地杯細嚐G'vine,細緻的檸檬香卻帶些甜美的花香氣撲鼻而來,雖討喜卻迴異於我習慣的植物香。)
喜愛喝Martini的人都有屬於個人的口感與選擇,海明威喜愛英國的Gordon's Gin與法國Noilly Prat vermouth調出一杯「非常冰涼又非常干爽」的Martini,包括搭配用的西班牙洋蔥都得先冷凍過;Colin Field為作家所調的Dry Martini,所用的水晶玻璃杯要冰至攝氏18.4度,Gin要冰到零度以下,不需要vermouth,只滴入少量的義大利橄欖油。但「要盡可能的快喝完它」這是倫敦The Savoy酒店American Bar的首席Bartender Peter Dorelli告訴我的,我曾在此Bar台喝他用Gordon's Gin為我調的Dry Martini與White Lady。Dorelli說,一杯好的martini要夠冰涼,這也是最好喝的時候。American Bar與Hemingway Bar、The Bemelmans Bar的Cocktails都是響譽世界,Dorelli於1963年進入Savoy酒店,1984年起在American Bar至2003年退休,有20年的Bartender歲月,豐富的調酒經驗與管理,因此常應邀到世界各地,包括曾到台北Shangri-La酒店指導與Cocktails有關的活動。
美國作家F. Scott Fitzgerald(費茲傑羅)所說,喝酒是「逃離」他加諸到故事裡的高張情緒。很多作家與記者都喜愛與酒為伍。英國女作家Olivia Laing於2013年寫了一本作家為什麼喝酒的書The Trip to Echo Spring:Why Writers Drink。她循著Tennessee Williams、海明威、費茲傑羅、John Berryman、John Cheever、Raymond Carver這6位美國名文學家常喝酒的地方去了解喝酒的心路歷程,The Economist、Financial Times都有書評。
因為喝酒,作家寫喝酒的心境總相當貼切,更為刻骨銘心,因此每次讀到這類文章,我總懷著愛、懼交織的心情,深怕投射到自己。紐約Post、Daily News的專欄作家、記者、編輯等諸多頭銜、有無數著作的Pete Hamill(1935-),這位愛爾蘭移民之子,於1994年所著的A Drinking Life回憶他的成長歲月與擁抱酒精的過程。生於波士頓的女記者、專欄作家Caroline Knapp(1959-2002)Drinking︰A Love Story(中譯本「酩酊:一個酒與愛的故事」,台灣商務出版。)寫她與酒奮戰20年的故事,以及喝酒、親情、愛情等細膩複雜的情懷,讀來讓我內心迴盪不已、眼淚直流。她是美國知名精神病醫學家Peter H. Knapp的女兒,但卻因為酒有「安慰人的特殊力量」(p.7),從此沉醉在酒精而無法自拔;甚至「因為畏懼性,因此喝酒面對它,喝酒經歷它。」(p.68)
Hemingway Bar「偏愛」文字工作者。1980、90年代我採訪報導諸多Leading Hotels of the World旗下會員酒店的新聞,巴黎Ritz酒店是其中的一員,當時(1997)的業務經理Astrid Mora告訴我,由於Hemingway Bar對文學非常嚴肅以待,因此為作家、記者、詩人與小說家設置郵箱的服務,收到的信陳列在Bar後方的箱子,首席Bartender Colin再拿給收信人。當年沒有網路,也不是今日身處iPhone、WiFi的「立即」時代,這種書信往來與人際互動的「老式浪漫」只成回憶。
不變的是,在Bar台向Bartender點酒、為你調酒時的彼此互動或是瞬間的眼神交會;以及Bartender在Stirred冰塊與酒發出輕脆的碰撞聲,或Shaking時發出厚實的攪拌聲。你知道一杯very cold、very dry的martini即將為你端上!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