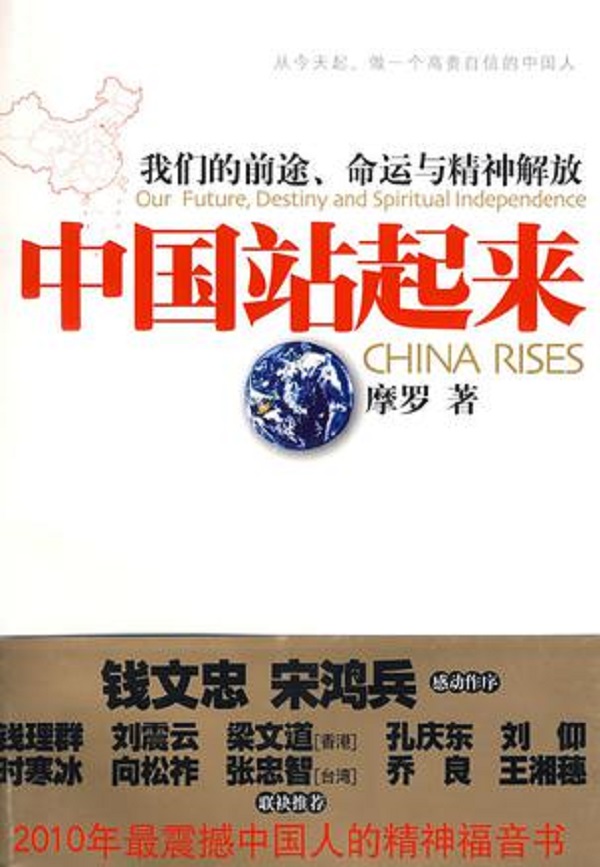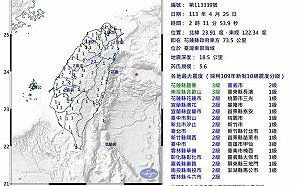「無賴們用愚蠢作了偽裝。」 ──威廉•布萊克
香港文化人梁文道為中國作家摩羅的《中國站起來》一書寫了一句評價:“真是文氣浩瀚,佩服。”沒有想到,摩羅真還將這句評語當作贊語,堂而皇之地印在封底——不知梁文道的名字能促進多少銷量。對於此種“唾沫自干”式的扮豬裝傻,對人性的黑暗估計不足的梁文道,大概只能以苦笑應對吧。
在被包裝得花枝招展的《中國站起來》一書中,摩羅有一句慷慨激昂的名言:“1909年,看不到中國的崩潰是有眼無珠。2009年,看不到中國崛起的趨勢也是有眼無珠。”在中文推特圈上,我看到一句更為精妙的點評:看不到中國的亂象卻夢囈崛起的,不是有眼無珠而是魚目混珠。
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至今,從《中國可以說不》到《中國不高興》,再到《中國站起來》,形成“文氣浩瀚”的“中國人三部曲”。這三本書的思想觀念層層遞進,清晰地顯示出當代中國法西斯主義思潮從萌芽到發展再到成熟的軌跡。這些充滿陰溝中的臭氣的爛書在票房上的巨大成功,無非依靠兩大靈丹妙藥:一是民族主義,二是民粹主義。在任何時代,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都能吸引一群如法國學者古斯塔夫•勒龐所說的“烏合之眾”。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正是法西斯主義的兩大思想淵源,也是中共的最後兩根救命稻草。
今天的中國正在沿著法西斯的道路高歌猛進,雷根執政時期的白宮顧問麥克勒丁博士,在《遠東經濟評論》上發表一篇題為《北京擁抱經典法西斯主義》的文章,他指出:“中國是經典的法西斯主義,第一個非常成熟的法西斯主義。少量的經濟自由,沒有政治自由,正是法西斯主義。”BBC中文網專欄作家蒙克在《當今中國、戰前德國與世界大戰警告》一文中說,把中國崛起可能挑戰世界秩序同一戰和二戰前的國際關係相提並論,似乎已經成為西方國際關係討論中的一個經常性話題。倫敦經濟學院的戰略問題學者克里斯托佛•考克(Christopher Coker)也認為,人類的理性被高估是造成歷史誤判的主要原因,中國目前的外交政策越來越喪失理性。
這是一個需要戈培爾的時代,有多少野心勃勃的失意文人自願獻身呢?這一次,摩羅押對了寶,不像1989年,這個單純的青年教師稀里糊塗地站在學生那一邊,去郵局拍電報要求罷免李鵬,結果差點被關進監獄——如今,中共黨魁習近平是強硬的民族主義者和民粹主義者,以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為新的信仰的摩羅,可以獲得一口金飯碗了。
“恥辱者”是如何變成無恥之徒的?
一九九二年,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既然總設計師說了不問姓“社”姓“資”,全民經商熱潮很快席捲全國,對物質的慾望成為國人唯一的慰藉。中國從“六四”之後被西方制裁和孤立的處境中解脫出來,加入全球化進程。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意識形態的真空越發凸顯,原有的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無法繼續蠱惑人心,民族主義和傳統文化熱便應運而生。官方的政治需要和商人的經濟利益一拍即合,一群狡猾的書商順勢炮製出《中國可以說不》,互聯網時代之前的第一代“憤青”粉墨登場。
《中國可以說不》的出現,是80年代具有理想主義激情的知識分子投靠主旋律的標誌性事件,也是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走向商業化的開端。《中國可以說不》這個名字頗值玩味,這是一個祈使句式,不是“中國必須說不”,而是“中國可以說不”,因為那時中國的權貴資本主義剛剛起步,中國還沒有跟西方叫板的經濟實力。鄧小平反覆教導說,要“韜光養晦”,不出頭,不爭霸。這幾名作者對當時官方色厲內荏的心態拿捏得恰到好處,對當時中共的內政與外交政策呼應得絲絲入扣。他們“說不”的對象是西方,而不是天安門屠殺之後手上沾滿鮮血的劊子手。他們深知,對西方“說不”不用付出任何代價,反而會得到當局的鼓勵和“愛國賊”們的掌聲;而對中共“說不”則萬萬不可,肯定會被封殺、被喝茶、被和諧乃至被投進監獄。
物換星移,到了2008年《中國不高興》出籠,作者依然是當初那幾個有文人氣的商人,世界金融風暴來勢洶洶,中國經濟“一枝獨秀”。在此背景下,這幾名作者與中國的當權者一樣,今非昔比、麻雀變鳳凰。如果說當年的“可以說不”僅僅是小心翼翼地表達“說不”是中國的一個選項和可能性,那麼如今的“不高興”則是理直氣壯地顯示某種實際存在的情緒。這種情緒激烈而狂躁,一方面迎合憤青群體“一無所有”的精神狀態,另一方面又試圖以撒嬌的方式展示給西方人看——我們不高興了,你們看著辦吧。
而一年之後橫空出世的《中國站起來》,則不僅是“不高興”的情緒的宣洩,更是站起來“欲與天公試比高”的具體行動。從《中國可以說不》到《中國不高興》整整用了12年,從《中國不高興》到《中國站起來》只用了12個月,這就是“中國崛起”的“加速度”。用摩羅的話來說,這是他“外爭國權”的一大壯舉。從憤世嫉俗的“恥辱者”進化到“真理部”的編外幹部,其間只需要一次華麗轉身。一個熱愛甘地的人,怎麼會對希特勒五體投地?誰也沒有想到,從甘地到希特勒,摩羅只走了短短幾步。
這10年來,摩羅取得的最大成功,就是由奴隷熬成奴才。記得80年代的中國有一部很走紅的電影,名叫《從奴隷到將軍》,摩羅當不了將軍,但在爭相賣身的御用作家中,也算是拔得頭籌。當大家都無恥時,無恥就不再是一種惡劣的品行;當“恥辱者”變成無恥之徒時,無恥就成了一張暢通無阻的良民證。學者蕭瀚說,摩羅的成名作《恥辱者手記》的真名該叫“中國人站起來了”,因為知恥而後勇;相反,《中國站起來》的真名該叫“恥辱者手記”,因為若不是無恥到某種程度,寫不出這樣的書來。借用北島的句式就是:無恥是無恥者的投名狀。
為此書作序的“不是經濟學家的經濟學家”宋鴻兵說:1949年,毛澤東揮筆寫下“別了,司徒雷登”;2009年,我們振臂吶喊“別了,美國模式!”這裡的“我們”顯然自視為“民族英雄”毛澤東的傳人。殊不知,當年剛剛告別司徒雷登的毛澤東,立即與蘇聯簽訂條約,出賣的國家利益之多,讓近代中國所有對外條約望塵莫及。左派對歷史和現實都很無知,對此我並不感到意外。對於“史詩般的吶喊”,我略略感到奇怪的是:偉大領袖在天安門城樓上宣稱“中國人民站起來”之後,在長達60多年裡,中國人民難道沒有站起來,或者說站起來一瞬間後又跪下去,直到2009年,才由一個文弱書生摩羅來宣佈中國站起來了?“站起來”是只能由偉大領袖宣佈的事實,哪裡輪得到弱不禁風的摩羅僭越,難道這個“臭老九”比偉大領袖還偉大?
《中國站起來》的作者自命為集“三個代表”於一身的國子監祭酒。書中最讓我作嘔的一句話是:“我看見工人農民的血汗正在澆築著中國崛起的基座。”那些被羞辱、被欠薪、被壓榨、被“黑煤窯”的工農大眾,那些在祖國“暫住”的農民工,是否認同這種“低人權優勢”,是否心甘情願地用血肉奠定“中國崛起的基座”?一不小心,數億工人農民就被這個當過“盲流”、如今登堂入室、躋身文化名流的文人給“代表”了。這個爬到權力基座中下層、分得一點殘羹冷炙的“不恥辱者”,對工農大眾的心思意念不感興趣,他不經授權而擅自“代表”人民的方式,跟電視上那些代言假藥的明星有異曲同工之妙。
這10年來,我眼睜睜地看著這個昔日的友人一步步地從“絶地戰士”變成“黑武士”。幾年前,我送給他一本我的新書《不要做中國人的孩子》,希望他瞭解那些死於天安門屠殺的孩子、死於三鹿毒奶粉的孩子、死於山西黑窯的孩子、死於四川大地震的孩子的悲慘遭遇,從而洞悉中國人民苦難的根源。在摩羅的成名作《恥辱者手記》中,有一篇題為《城裡的姨媽》的散文,栩栩如生地描述了城市貧民的困窘與堅韌,曾讓我感動不已。造成千千萬萬“城裡的姨媽”無盡苦難的,造成千千萬萬孩子死不瞑目的悲劇的,難道是早已被毛澤東“別了”的西方殖民者嗎?在天安門廣場上向手無寸鐵的民眾開槍的,難道是裝備精良的美國大兵嗎?大饑荒中數千萬民眾被活活餓死,難道是因為萬惡的美帝或蘇修的封鎖嗎?近年來,孫志剛之慘死、唐福珍之自焚、趙連海之被囚、錢雲會之被殺、雷洋被“嫖妓死”,難道是美帝和日寇在背後施加黑手?
這些罄竹難書的苦難,並非“帝國主義”造成的,乃是盤踞在中國人頭上的中共政權造成的。動了中國人乳酪的,不是憤青們臆想出來的“亡我之心不死”的外敵,而是獨裁專制的共產黨和孕育這個黨的中國人自身的劣根性。這就是卑之無甚高論的常識。無視此常識的人,要麼是知識結構存在嚴重缺陷,要麼是道德品質墮落極深。若是前者,還有救治之法,網上有一名90後的中學生說,以前他是民族主義“憤青”,學會“翻牆”看牆外的世界之後,不到一個月就覺悟成了自由主義“右派”;但若是後者,那就無藥可救,因為對於這類人來說,不墮落,就沒有辦法實現賣身求榮。
如今,在這個無視常識、扭曲事實的“過於聰明的中國文人”的行列之中,在“余含淚”與“王羡鬼”之外,又多了一個昔日哭天喊地的“恥辱者”。
背叛自由,以毛為聖
《中國站起來》是對80年代啟蒙主義和自由精神的全盤否定,是對“五四”倡導的民主和科學價值的全盤否定,是對近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尋求有尊嚴的生活方式的努力的全盤否定。與之對應的,這本書也是對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和習近平時代的權貴資本主義和次法西斯主義的全盤肯定,是對毛澤東時代的紅色極權主義的全盤肯定,是對慈禧太后和義和團式的閉關鎖國、殘民以逞的國策的全盤肯定。一貶一褒,表明作為曾經追求民主自由的當代知識人之一員的摩羅,選擇以最卑賤的方式向權力下跪——難怪那個喜歡三跪九叩的“古禮”並親自實施的錢文忠教授,欣然為之作序。
德國思想家西奧多•阿多諾說過,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同樣,“六四”屠殺之後,任何向“國家”拋媚眼的行為,都是對死難者的侮辱。某些學者名流忘記了包括中國人生活在“動物莊園”裡的可悲處境,分到一點糧草,便聲嘶力竭地為“和諧社會”和“大國崛起”充當吹鼓手。當然,他們知道這個社會不夠和諧,老百姓對“今上”有諸多不滿。這時,就需要奧威爾所說的“公共污水溝”轉移公眾注意力。西方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便成了順手牽來的“替罪羊”。
當局對於反西方的“吶喊”從來都鼓勵和縱容。當反日遊行人山人海之際,當局特意給眾人準備好扔向日本大使館的磚頭。這一次,《中國站起來》倡導的反擊西方的口水戰,官方亦樂觀其成,動員若干中央級媒體為其提供周到的“後勤支持”。雖然摩羅在上個世紀90年代未曾出現在中宣部的黑名單上,但“知錯能改,善莫大焉”,浪子回頭金不換。從黑名單躍上紅名單,如同鯉魚跳龍門。將“倚天劍”賣予“帝王家”,帝王不會讓投誠者吃虧。
這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既然為帝王而戰,那麼帝王的敵人,便是摩羅的敵人。除了帝國主義者和殖民主義者覬覦我天朝大國的陰謀之外,還得像當年劃“右派”一樣划出一群賣國賊和漢奸來。摩羅找到的“漢奸”的代表人物,便是蔡元培、陳獨秀和胡適,當然還有他要“謝本師”的精神導師魯迅。他說,如果不是這些“漢奸”的風言風語、自我菲薄,中國的偉大崛起又怎麼會遲到半個多世紀呢?
摩羅用一連串煽情而空洞的排比句攻擊胡適,如此惡毒的文字即便放在50年代初毛澤東掀起的批判胡適運動中也毫不遜色——“最無能的男人總是抱怨祖宗沒給他留下更多的財產,最無知的精英總是抱怨大眾過於愚昧聽不懂他的偉大思想,最無恥的失敗者總是歌頌強盜劫掠時打斷他一條腿給他開創了生命新境界,胡適博士三者兼備焉。”如果當年毛澤東讀到如此文字,說不定龍顏大悅,提前將姚文元的職位賜予摩羅。然而,胡適不是用這種粗陋的謾罵就可以打倒,余秋雨一九七四年在文革派控制的媒體上發表《胡適傳》的時候就嘗試過了。作為胡適反面的余秋雨和摩羅,不過徒增笑柄而已。
“五四”不是不可以反思,思想史學者張灝以“幽暗意識”反思“五四”激進的社會改造思路,是一種極好的反思方式。同樣,胡適不是不可以批評,胡適確存在某些侷限甚至錯誤,如過於信服杜威的實用主義。但是,給胡適扣上“賣國賊”的帽子,不是批評,而是污衊。我可以斷言,摩羅沒有讀過《胡適全集》、《胡適日記》等原始資料,也沒有研究過胡適的若干著作。這是在展開嚴肅的批評之前必須做的功課。胡適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熟悉與研究,比起葉公好龍的毛澤東不知強多少倍,更是既自卑又自戀偏偏不讀書的摩羅所望塵莫及。對中國傳統文化,胡適是“去其糟粕,取其精華”,毛澤東和他的精神後代們則是“去其精華,取其糟粕”。
歷史學家余英時在《胡適與中國的民主運動》一文中指出:“胡適雖以‘反傳統’著稱,但是他在推動中國的民主運動時,卻隨時地不忘為民主、自由、人權尋找中國的歷史基礎。他承認中國歷史上沒有發展出民主的政治制度。但是他並不認為中國文化土壤完全不適於民主、自由、人權的移植。”胡適在晚年發表的演說《中國傳統及其將來》中,認為中國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和理性精神足以構成接引民主與科學的“中國根柢”。對此,余英時闡發說:“這一點對於今天中國大陸爭取民主、自由的人更具有重要的啟示。胡適從不把中國傳統看成籠統一片;相反的,他對傳統採取歷史分析的態度,他要辨別其中哪些成分在今天還是有生命力的,哪些是已經僵死的。”這樣的論述跟《中國站起來》一書中唾沫橫飛的謾罵相比,哪一個更接近事實與真相呢?
畢竟胡適是死老虎,在批判完胡適之後,摩羅立即將矛頭對準當下所謂的“崇洋媚外”者,他描述說,“中國的某些精英人物就像西方殖民勢力安置在中國的思想警察”。這種說法跟幾年前攻擊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特務的王紹光暗中唱和。他們知道哪些人是官方不喜歡的人,攻擊、辱罵乃至妖魔化這些人,可以得到官方的賞識和獎勵。
很不幸,我就是持續多年不能在中國發表一個字的、所謂“精英人物”中的一員。作為被當局封殺者,我如何完成“西方殖民勢力”任命給我的“中國的思想警察”的任務呢?我只知道每年有幾十天時間,國保警察在我門口站崗,不准我踏出家門及會見朋友。將警察的受害者污衊為“思想警察”,只有摩羅才有如此豐富的想像力。僅有想像力是不夠的,還要有告密的行為。這種卑劣而陰險的告密行為,連普通的五毛黨都不屑去做,摩羅卻樂此不疲,可以載入學者冉雲飛撰寫的《中國告密史》之中。
摩羅自以為讀了幾本“人類學”著作(其實大多是西方極左派的胡編亂造之作),就可以對中國和世界局勢指點江山、激揚文字。他既反對普世價值,也反對近代化和全球化。在他看來,“自由貿易的真相是搶劫”,“自由市場的真相是槍炮和霸權”,“自由競爭的真相是不讓別人發展”。按照他的設想,中國乾脆退出世貿組織,乾脆像北韓一樣切斷與世界聯繫的網絡,乾脆像毛時代那樣實行統購統銷的計劃經濟。那才是中國最“獨立自主”的時代。
毛澤東曾賭氣說,我要帶著江青上井岡山打游擊;而摩羅給未來中國開出的藥方則是“尊王攘夷”,這個藥方跟毛澤東賭氣的狠話相映生輝。這些搖著羽毛扇的縱橫家,真該去投靠毛新宇少將,通過運籌帷幄、合縱連橫,將毛三世推上皇位,如此方可實現其帝王師“澄清宇內”之夢想。
從揭露說謊到以說謊為榮,真如聖經中所說,人心比萬物都詭詐。我想起10年前我與摩羅、孔慶東一起編纂的《審視中學語文教育》一書。該書因質疑魏巍《誰是最可愛的人》、揭露韓戰之真相,遭到教育部和中宣部圍剿,出版社也被停業整頓。如今,摩孔二人“覺今是而昨非”,恨不得跑到北韓去當宣傳部長。此二人變化之快,讓人瞠目結舌。韓寒說過,通往北韓的道路,是由每個人的沉默鋪就的;他卻不知道,中國還真有“直將北韓當天堂”的、“過於聰明”的“副教授”和“副研究員”(由於他們的出色表演,前面的“副”字很快就去掉了)。
同樣是以“中國”為論述對象的著作,在《中國站起來》一書中,我看到的是顧影自憐和胡言亂語;而在財經作家蘇小和的《我們怎樣閲讀中國》一書中,我看到的卻是理性與睿智——蘇小和在《每個人的全球化》一文中寫道:“我看見新一代的中國人在相對寬闊的信息通道中自由遊走,在財務相對自由之後,年輕的人們開始追求行走的自由和心靈的自由。雖然仍有人坐井觀天,仍有人畫地為牢,但世界已經為我們打開,每個人都在全球化之中,只要有足夠的懷疑精神,只要學會在多元狀態下思考,我們就再也不會輕易被遮蔽,被矇騙了。”換言之,全球化就是自由化,自由化就是去愚昧化,沒有人可以依靠昔日的名氣充當別人的“導師”。難怪那些“左狂人”對“自由”二字恨之入骨,因為在這個信息越來越自由流通的時代,要想騙人可沒有信息封閉的毛時代那麼容易了。
“準法西斯”的“真人秀”
《中國站起來》是一本向希特勒的《我的奮鬥》致敬的作品。摩羅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就反抗西方而言,希特勒是有其合理性的。”以此推導,集中營和大屠殺也是有其合理性的。在中國之外的任何地方,恐怕找不到幾個所謂的“知識分子”敢於如此不加掩飾地挑戰人類的道德底線——伊朗總統內賈德算是摩羅值得尊敬的戰友之一。
《中國站起來》一書,一邊向當權者諂媚,一邊煽動仇恨、鼓吹暴力,其文字之粗糙、審美之醜陋與精神之卑瑣互為因果。這正印證了我一直以來的觀點:思想的敗壞必然導致文字的敗壞。且看作者自己概括的中心思想:“本書所要強調的是,我們要儘早擺脫殖民時代所加給我們的精神創傷,我們應該挺起精神脊樑,以飽滿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走向崛起之路,以逢山開路、遇水架橋的偉大氣魄,將今天崛起的趨勢變為明天崛起的現實。”正是無數像小學生作文一樣的大話和空話,支撐起這本臭不可聞的垃圾書。乍一看,還以為是大躍進時代“農民詩”的集錦。優美的中文被糟蹋到此種地步,讓人目不忍睹。
左派為了實現烏托邦的狂想,不惜殺人如麻。摩羅在書中模仿希特勒、毛澤東和波爾布特的語氣宣佈說:“我們甚至應該以戰爭動員的方式,組織全民族的力量,為保證這一次崛起的成功而殫精竭慮,誓死拚搏。”連中共當局都不敢輕言“戰爭動員”,這個昔日高舉人道主義旗幟的作家,卻如同當年在北京城殺人殺紅眼睛的嗜血的士兵一樣,公然喊打喊殺。摩羅儼然以國防部長自居,更要像當年的慈禧太后那樣宣佈向萬國開戰。
可惜,共軍從來就不具備抵禦外敵的勇氣,從來就不曾有“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的豪情,他們只會屠殺本國民眾,從天安門殺到西藏,再殺到新疆,如魯迅所說,他們只知道屠戮婦女和嬰孩!這樣的一支軍隊無法滿足這個內心怯懦的文人的戰爭夢。那麼,要過戰爭癮,摩羅只能報名去參加塔利班或伊斯蘭國。
虧得摩羅還自稱為佛教徒,跟許多人像模像樣地談經論道。當西藏有那麼多溫和的僧侶和佛教徒遭到中共軍隊殺戮時,當達賴喇嘛被中共官僚辱罵為“人面獸心”時,他為何一言不發呢?他哪有半點佛教徒的慈悲與愛心呢?摩羅先生,不要用佛教徒的身份來掩蓋法西斯主義者的本質。法西斯主義是如同瘋牛病一樣的病毒,它徹底敗壞人的思維和理性,甚至道德和倫理。我們與希特勒、戈培爾、史達林、毛澤東之間的不同,不僅僅是觀點的差別,而是靈魂上的迥異。患上法西斯病症的人,不僅僅觀點出格和邏輯混亂,更是人品全然敗壞。
法西斯主義的病毒讓人的精神鈣化,甚至永遠無法復原。我很少見到法西斯主義者覺悟成為民主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的,我倒是時常見到民主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蛻變為法西斯主義者,摩羅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曾經被摩羅視為精神導師、與之有過長達30年友情的學者吳洪森,一針見血地指出其“變臉”的真相:“在表面的狂熱之下,是出於功利主義的選擇。”是的,沒有信仰的支撐,有幾個人可以靠著個人的力量,勝過殘酷的打壓、無邊的寂寞與長久的清貧呢?那種重返文化舞台的虛榮心,那種一字千金的貪婪,眼目的情慾與今生的驕傲,會讓高度自戀的文人急病亂投醫。為了一己之私利,可以扭曲歷史,可以顛倒黑白,可以泯滅良知——有多少文人走上這條不歸路?
摩羅辱罵胡適“最無知”、“最無能”、“最無恥”,因為胡適批判的對象正是他所倡導的殘忍、野蠻與愚昧。胡適說過:“今日還是一個大家做八股的中國,雖然題目換了。小腳逐漸絶跡了,夾棍板子、砍頭碎剮廢止了,但裹小腳的殘酷心理,上夾棍打屁股的野蠻心理,都還存在無數老少的心靈裡。今日還是一個殘忍野蠻的中國,所以始終還不曾走上法治的路。”《中國站起來》便是這樣一本鼓吹小腳、夾棍板子、砍頭碎剮的書。
摩羅本名萬松生,其筆名取自魯迅的《摩羅詩力說》,一度被錢理群教授譽為“精神界戰士譜系的自覺的傳承者”。如今,錢理群對其惟有一聲嘆息。而魯迅早已料到“城頭變幻大王旗”的身後事,早已料到“被背叛的遺囑”是一種必然。既然與魯迅絶交、與舊我絶交,不妨將這個筆名歸還給魯迅,重新取一個向毛澤東致敬的筆名吧。我建議美其名曰“萬愛東”,就是萬松生愛毛澤東,或者是萬分熱愛毛澤東,如此就能跟污衊上訪者是精神病的北大教授孫東東(以及“三媽教授”孔慶東)稱兄道弟了——三個“東”可唱一台戲。
真人秀,說到底還是“秀”。到了最後,表演者分不清哪些是表演,哪些是自己的生活。在中國,鼓吹愛國主義、民粹主義這些玩意的人,從來都不當真,清楚地知道這是“真人秀”。希特勒是個徹頭徹尾的法西斯主義者,摩羅和他的朋友們則是“言論的法西斯”——他們不敢像希特勒那樣真的動刀動槍,這是中國的“幸運”嗎?摩羅也沒有去伊拉克和阿富汗打游擊,他只能算是“準法西斯主義者”,以法西斯主義的雜耍賺點小錢而已。別看他嘴上信誓旦旦,如果生活在抗戰時代,他或許就是才華與風雅都要遜色九分的胡蘭成。
這類人從未愛過國家,從未愛過身邊的同胞,從未愛過孫志剛、唐福珍、李旺陽和陳光誠,這類人只愛自己,只愛權力與金錢。他們是儒而非儒,是佛而非佛,滿口甘地,滿紙特蕾莎修女,骨子裡還是蘇秦與張儀,還是希特勒與毛澤東。對於這種大言不慚的“愛國賊”,英國學者C.S.路易斯指出:“他愛國,是因為他認為祖國強大而美好,即因她的優點而愛她。她像一個運轉良好的企業,身在其中滿足了他的自豪感。她若不復如此,情況會怎樣?答案清楚明了:‘我們便速速棄之而去。’船隻下沉時,他會棄船而去。這種愛國主義出發時鑼鼓震天、旌旗飄揚,實際卻趨向變節和沒落。”
雖然摩羅恨透了魯迅,我還是要引用魯迅的名言來教導他,魯迅說:“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樑。”是的,真正的愛國,乃是愛這片多災多難的土地和生活於其上的多災多難的同胞;真正的愛國,乃是奮起對抗那些讓大多數民眾都難以“好好生活”的特權階層與權貴集團。真正的愛國者是劉曉波,是丁子霖,是蔣彥永,是劉賢斌,而不是那些“說不”的中國人、“不高興”的中國人和“站起來”的中國人。
這篇文章,算是割席斷袍。對於這個靈魂跪下來、嘴裡卻宣稱站起來的“恥辱者”,我只剩下一句話可說:“你把良心典當到地獄裡,你拿什麼贖回來呢?”
附記
本文原名為《誰動了中國人的乳酪?——從<中國站起來>等“中國三部曲”看當下的法西斯主義思潮》。完成之後,又做了一定的修訂與補充,並改為新題目。最近十多年來,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正在成為中國官方的新意識形態,在此過程中,還會有若干像摩羅這樣的御用文人投入鼓吹者的行列。從昔日倡導自由、民主的獨立知識分子,變成如今狂熱的毛派和民族主義者(法西斯主義者),“摩羅變臉”在當代中國不是孤立的個案,而是一種有普遍性的現象,有必要作出分析與探討。
2010年第8期和第9期的《讀書》雜誌連載了學者許紀霖的評論文章《走向國家祭台之路》。該文以《中國站起來》一書的問世和作者的轉向為個案,分析了當今中國的“民族主義狂飆”。作者認為:“這股狂飆,從反西方與反啟蒙出發,配合中國崛起的時代背景,從守護民族傳統的文化保守主義逐漸發展為崇拜國家的政治保守主義,最後聚焦於中國道路、中國模式的另類現代性訴求。”
作者指出,一些知識分子之所以由人道主義蛻變為虛無主義,並走上國家乃至權力的祭台,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浪漫主義所具有的雙重曖昧性,使之與人道主義分道揚鑣。但我認為,摩羅等人“轉向”的原因並沒有如此複雜,說到底,是尋求真實可靠的信仰而不得,最後成為個人名利之心的俘虜。他們選擇被招安的命運,一言以蔽之,就是“屁股決定腦袋”。

中國作家摩羅。 圖:翻攝優酷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