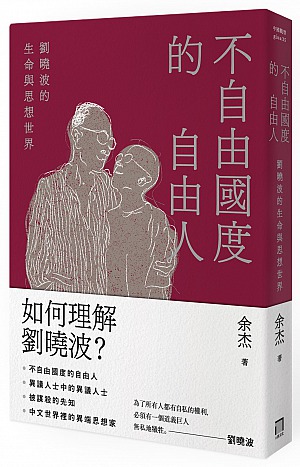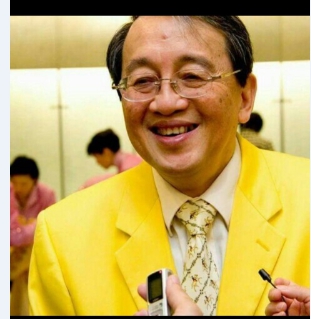不許殺人:從「六四」屠殺到楊佳襲警
在「六四」期間,以及整個八十年代中後期,劉曉波常常受到的批評,是「激進」、「狂妄」、「愛出風頭」、「個人英雄主義」等;近年來,他繼續遭到各種指責,這些指責變成了「投降派」、「跪著造反」、「革命不徹底」、「與當局妥協」等。吊詭的是,那些批評者簡直就是以「昔日之劉曉波」否定「今日之劉曉波」,蘇曉康感歎說:「劉曉波因『文化激進』而備受批評,又因『政治溫和』而同樣備受指責,受『兩面夾擊』如是者,在中國又曾有誰?」
「不許殺人」是劉曉波從「六四」慘案中汲取的血的教訓。他不僅反對政府對和平請願民眾的武力鎮壓,也反對民間人士以暴易暴的「原始正義」。「原始正義」是劉曉波提出的一個重要概念。這個概念早在九十年代初便在他心中醞釀,隨著二十一世紀以來中國貧富懸殊日漸擴大、官民衝突趨於激烈,他的思考逐漸成熟。他指出:「如果正義的實現必須以法外的暴力流血為代價,那麼這樣的正義至多是原始性的復仇正義。」毫無疑問,「原始正義」是一個超前概念,它一時難以為中國知識界和普通民眾接受,但肯定會成為中國人為世界貢獻的一個涵義豐富的政治學辭彙。如同吳思創造的「潛規則」一樣,劉曉波創造的「原始正義」必定是人們描述轉型中國時無法繞開的概念。
「原始正義」的概念,在楊佳案的討論中備受關注。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在上海市公安局閘北分局發生北京青年楊佳襲警導致六名警察身亡、五名警察及工作人員受傷的事件。楊佳案在審理過程中,關於律師委任、犯罪嫌疑人精神病鑒定、楊佳母親的離奇失蹤等程式爭議頻出。
最後,法院判決楊佳「故意殺人罪」罪名成立並處死刑。此案中關於是否缺乏對公安警察的安全保護,警察執法、與民眾應對是否合理、程式正義,司法公正和社會公正等問題,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討論。
在楊佳案件審理期間,一批民間人士起草並發佈了《關於特別赦免楊佳先生的公民建議書》。這份建議書由艾未未、茅于軾、杜光、于浩成、戴晴、張祖樺等數十人領銜,徵集到三千多人的連署。這份建議書指出:「楊佳先生在長期經正常合法途經尋求權利補償不果且得不到公正司法救濟的情況下,採取極端手段,導致了這場悲劇。……如果最高當局不能採取特殊的司法救濟,必然給全體國民、國際社會留下整個政權、國家機器在圍剿一個受到不公正對待、血氣方剛的二十多歲青年的印象。」耐人尋味的是,雖然這份文件的簽署者很多都是劉曉波親密的朋友,九十年代以來幾乎參與所有重要聯署信簽名的劉曉波,卻並未參與此次簽名。
網路上更是掀起讚美楊佳的聲浪。艾未未為楊佳拍攝紀錄片,許多年輕網友將楊佳描述為「大俠」和「英雄」,甚至訴諸於《三國演義》和《水滸傳》的民間文化傳統,將楊佳視為正義的化身,視為劉關張和武松、魯智深、李逵的「轉世靈童」。在MSN上,許多人將楊佳的名言「你不給我一個說法,我就給你一個說法」當作簽名;在推特上,許多人將楊佳的照片設置為頭像。楊佳被處死之後,其墓地也成為人們憑弔的名勝。楊佳成了一個負載民間複雜的不滿情緒的符號。然而,楊佳襲警的方式,真的是中國順利步入公民社會的最佳選擇嗎?
楊佳案若發生在西方國家,只是一個普通的惡性刑事案件,但發生在公權擴張、民權萎縮、貧富懸殊、司法不彰、民怨沸騰的中國,就成了一起具有標誌性的社會事件。楊佳案,讓人們從各個角度,看到中國與憲政制度的差距。作為一名關懷現實的「公民知識份子」,劉曉波就此主題先後撰寫了多篇文章,系統地闡釋了自己的看法。
在論述楊佳案件時,劉曉波指出:該案不是偶然的事件、不是孤立的個案,而是中國社會的平衡性斷裂的標誌之一。造成楊佳之死以及六名警察被他殺害之悲劇的罪魁禍首,是中共當局迷信暴力的政策。近年來,中國已經變成名副其實的警察國家:警察被推到第一線處理官民之矛盾,警察成為官員濫用公權力傷害民眾的工具,亦成為鋌而走險的少數民眾報復的對象。劉曉波評論說:「中國社會彌漫著日益嚴重的暴戾之氣,其主要根源,不是來自民間的暴力偏好,而是來自官權的暴虐統治。……現在,眾目睽睽之下,上海當局在楊佳案上的濫權,中央政權對上海當局濫權的默許,只能證明執政者仍然迷信暴力專政的統治方式,現行體制仍然是濫用警力和司法不公的庇護所。官權如此作為的民間效應,只能加強民間逆反,成倍地放大了這種暴戾氣氛,產生更多的民間暴力反抗,製造出更多的『大俠』或『英雄』。」顯然,劉曉波的批評對像首先是製造暴力和暴力文化的掌權者。
劉曉波對案件審理過程中的一系列「非常情況」作出強烈譴責。比如,楊佳的母親被綁架後關押在精神病院、審判在秘密狀態下進行。「如果說,楊佳的刀光及輿論效應是戳破了『和諧』假像的利劍,那麼楊母的出現就是指向中共官權的另一柄利劍,既戳穿上海司法當局的彌天大謊,也刺破了中國司法制度及依法治國的面紗。」他指出,司法公正的喪失將對社會穩定帶來致命的危害。「公共輿論對楊佳案的期望也不複雜,不過是希望司法公正的實現,至少讓楊佳『死得明白』。」但是,此案審理過程的種種謬誤表明,中國並無獨立之司法權,作為黨的一大分支機搆的「政法委」,包攬所有重大案件的最後判決。當局傲慢地認為,包括司法在內的一切盡在其掌握之中,卻茫然不知一個社會的司法公正徹底喪失之際,也就是這個社會穩定的堤壩最後破裂之時,「中國司法機構的信譽已經在民心中的死亡。楊佳死了,但覺醒的民意不會隨之死亡」。
底層暴力有其社會基礎。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認為,長期以來引發暴力傾向的,是「貧窮、剝奪、忽視和羞辱」,「義憤」為「報復」行為打下伏筆。以此而論,楊佳以死相爭的決絕不無可憫之處。但是,在那些高聲為楊佳叫好的聲音當中,劉曉波嗅到一種從義和團到紅衛兵一脈相承的「烏合之眾」的氣味。他對這種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交織的味道尤為敏感。他不同意艾未未和某些維權律師將楊佳的殺人行為合理化甚至英雄化的言論,他的觀點與《關於特別赦免楊佳先生的公民建議書》存在顯著之差異,他提出的民間社會不能被「原始正義」牽著鼻子走的觀點,在網路上引發暴風驟雨般的批評意見。這是劉曉波與中國正在興起的民粹主義思潮之間的一次正面交鋒。
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呼應與合流,是近年來中國出現的新的思潮和現象。研究民粹主義的學者保羅•塔洛特-加龍省指出:「民粹主義常常傾向於用其所選擇的民眾的理想化的觀點來確定自身,並把它們置於相似的理想化的背景之中。」許多知識份子也許能抗拒金錢的誘惑,卻難於抗拒名聲的誘惑——尤其是在民間的名聲。一旦批判民粹主義、批判「多數人的錯誤意見」,就有可能損害這種民間的聲望。劉曉波的可貴之處就在於,在對所有的公共事件發言時,不以個人名望為念,而以真理為尺規。他忠誠於真理,不惜得罪多數人、得罪朋友,他敢於充當「飽受爭議的少數派」和「異議人士中的異議人士」的角色。
劉曉波認為,無論從客觀效果還是就價值立場而言,「楊佳式的復仇」對中國社會轉型都有害無益。他對楊佳的反抗方式不予認同,在任何場合都不隱瞞這一觀點:「如果暴力反抗是個人復仇的主動施暴,其結果是雙方的生命代價,那就是沒有贏家的玉石俱焚,也就談不上正義。」他沒有在那份呼籲特赦楊佳的公開信上簽名,除了他作為美國意義上的保守主義者並不同意完全廢除死刑的立場以外,還有他對楊佳瘋狂殺戮行為的反感。
在這一點上,劉曉波與法學界前輩江平的看法是一致的。江平指出:「你楊佳受到再大的委屈,你對社會發洩私憤,對公安機關發洩私憤,殺了六個無辜警察,道理何在?這些人有什麼罪?」在一次演講中,江平陳述這一觀點之後,有個青年學生威脅說,如果手中有雞蛋,會立即用雞蛋砸他。江平與劉曉波一樣,連共產黨的威逼利誘都不怕,又怎麼會怕被庸眾的雞蛋「砸」呢?
劉曉波指出,從客觀效果來看,這種個體性的殺戮,非但不能震懾那些作惡的警察,反而會引發當局更加瘋狂的鎮壓。「如果楊佳襲警的發生讓民間相信暴力,產生對一場暴力革命的期待,其結果就是更多的暴力反抗的發生。而獨裁政權的應對只能是政府不斷強化政治恐怖,不斷加強鎮壓的力度,只能進一步弱化本來就弱小的民間維權力量,中國的社會生態也只能從『壞』走向『更壞』。」劉曉波看重的是一種健康、理性的社會生態的培育,而非瞬間的「快意恩仇」,但他的這番良苦的用心,很難為被激情和仇恨左右的被侮辱者和被傷害者所理解。
從價值立場而言,面對網上對警察被殺的一片叫好之聲,劉曉波反問說:那些被楊佳殺害的警察是否「罪有應得」?是不是所有穿警服的人都「死有餘辜」?他認為:「楊佳不是英雄或大俠,因為他結束了六個生命。難道對生命的珍重還要區分警民,難道僅僅因為警察的身份被殺就是活該?即便被殺警察中可能有迫害過楊佳的人,也是罪不當誅。」雖然這些年來劉曉波本人是警察濫權的最大受害者,但他認為,那些被楊佳殺害的警察是無辜者,不能因為他們從事警察這一職業,便自然而然地成為被行兇的對象。且不說他們並非傷害過楊佳的那幾個警察,即便就是那幾個作惡的警察,也應當通過司法程式對其行為調查、審判和追究——當然,目前來看,暫時還沒有實現這一目標的可能性。但並不意味著任何人就可以立即啟動「個人執法」,施行「私刑」。
如果所有警察都該殺,將此邏輯往下推演,是否所有公務員都該殺,是否所有共產黨員都該殺?這樣,要殺多少人才能讓中國變成一個「純潔」與「公義」之國?這種思路與做法,與當年毛澤東奪取政權之後,掀起「三反五反」運動,大肆屠殺國民黨政權遺留下來的黨政軍人員及其家屬的暴政有什麼區別呢?
劉曉波對頌揚楊佳殺人行為的民粹主義言論充滿憂慮,當民間被「原始正義」壓倒之時,就不自覺地跟反抗的對象達成「精神同構」,這是劉曉波最擔憂的情形:「如果主流民意只有通過楊佳式復仇來宣洩心中的壘塊,那麼中國的民智就仍然是『咬住仇,咬住恨,仇恨入心要發芽』的犧牲品。如果以民為敵的官權暴虐與以官為仇的民間暴戾相互激蕩,那麼只能造成以暴易暴的惡性循環,今天的局部性以暴易暴很可能發展為全局性以暴易暴。不要讓仇恨和暴力毒化今天的民間維權和中國的法治進程!」
惟有非暴力才能通向新文明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劉曉波從紐約啟程回國那天,時任《時報週刊》總編輯的臺灣朋友杜念中開車趕到胡平家,送給劉曉波兩套非暴力政治學專家基恩•夏普的著作。不知彼時心潮起伏的劉曉波,在飛機上是否翻閱過該書?甫一回國,在學運的洪流中,他肯定沒有時間和心情仔細閱讀此書。也不知這兩套書後來的命運如何,是不是落入那些抄家的警察手中?
有人認為,非暴力僅僅是一種可以選擇的手段,而且還得辨析對手是誰——比如,在面對具有基督教信仰、有妥協傳統的英國殖民者時,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的策略是有效的;但在面對那些更加殘暴的獨裁者和政權時,非暴力的策略就是無效的,只能採取武裝鬥爭的方式。劉曉波則認為,非暴力不是一種手段,而是一種價值;非暴力適用於任何情境之中,而不是在權衡對手的道德與倫理狀態之後的一種選擇。「當民間反對者必須面對被強加的暴政及其苦難之時,作為反抗的一方,應該具有一種超常堅韌的非暴力反抗能力,那是一種直面暴虐的超常勇氣,一種忍受痛苦和屈辱的超常能力,用仁愛面對仇恨,以尊嚴面對羞辱,以寬容面對偏見,以謙卑面對傲慢,以理性面對狂暴,最終逼迫加害者回到理性和平的規則中來,從而超越『以暴易暴』的惡性循環。」從「八九」學運到《零八憲章》,非暴力成了劉曉波堅定不移的信念與信仰。
非暴力絕非軟弱。考察各國人權運動的歷史,可以發現一條共同的軌跡:暴力從未帶來自由與和平,只有非暴力才贏得解放與幸福。非暴力之中蘊含的力量,超乎暴力信奉者們的想像,非暴力並不是弱者的選擇和「沒得選擇的選擇」。非暴力運動之父甘地指出:「非暴力像活動中的鐳。無論量多小,它一旦介入腫瘤的生長就將無聲、平穩而永不停息地發揮功效,直至將有病的肌體組織完全轉化為健康的組織。同樣,一點點非暴力也會微妙無聲地發揮效力,並在不知不覺中使整個社會日新月異。」換言之,只有以非暴力對抗暴力,才能改變與轉換暴力。
非暴力思想的形成,對任何人來說都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即便宣稱「今天的問題不是要暴力還是非暴力的問題,而是要麼選擇非暴力,要麼選擇滅亡」的馬丁•路德•金,早年在是否選擇非暴力上,也有過長時間的猶豫。在大學時代,「在這一時期,在解決社會問題方面,我對愛的能力已感到絕望。我認為唯一能解決種族隔離問題的方法是武力暴動。」跟劉曉波一樣,金也曾是尼采哲學的推崇者:「對愛的信心受到尼采哲學的動搖。尼采對權力的榮耀是他從對普通人的蔑視中發展而來。他攻擊了整個希伯來-基督教的道德體系,包括敬虔、謙卑的美德,對未來美好世界的關注以及對苦難的態度,尼采認為這是對軟弱的讚美,是不得已的心甘情願。他期待超人的出現,超人超過人就像人超過猿一樣。」但是,形形色色的哲學和思想並未讓金找到人生的出路,最後的出路是在甘地那裏找到的:「我在邊沁和穆勒的實用主義、馬克思和列寧的革命方式、霍布斯的社會契約理論、盧梭的『返回自然』的樂觀主義、尼采的超人哲學中均未獲得學術上和道德上的滿足,我在甘地的非暴力抵抗哲學中找到了。」金從甘地的非暴力學說和聖經的教導中汲取到無窮力量,並以此領導黑人群眾爭取人權。
曼德拉也是如此,他有更加明顯的從暴力轉向非暴力的過程。早年,曼德拉曾主張用武裝鬥爭反抗白人政權,他被授權組建與非洲人國民大會保持獨立的新的軍事組織,名為「民族長矛軍」。「我從來沒有當過兵,從來沒有打過仗,也從來沒有朝敵人開過槍。但是,組建軍隊的任務卻落到了我的頭上。」曼德拉學習了大量的武裝鬥爭特別是遊擊戰爭的文獻,如德尼斯•賴茨寫的描述布林戰爭期間布林人的遊擊戰術的《突擊隊》,如格瓦拉、毛澤東、卡斯楚的著作,他甚至在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中發現「是毛澤東的決心和非傳統思想把他引向了勝利。」然而,此後殘酷的武裝鬥爭讓事態日漸惡化。曼德拉意識到,這不是一條正確的道路:在國內,越來越多無辜者的生命被犧牲,離勝利的目標卻越來越遠;在國際社會,這種方式得不到同情和支持,當曼德拉被關進監獄時,「大赦國際從未支援過我們,這個組織不可能為堅持暴力的人撐腰」。曼德拉在獄中每看到一篇暴力衝突導致平民傷亡的報導的時候,都心痛如刀攪。後來,當暴力衝突席捲全國,他終於意識到,尋求和平的時刻到來了。
非暴力抗爭不是夢囈,而是被印度、南非等國家的國家獨立或社會轉型的歷史驗證的成功之路。它也是中國憲政轉型惟一可行的道路。在每一次衝突之中,當人們在槍尖上尋求完美時,最後的結局必定是暴力氾濫。一九八零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阿根廷人權活動家埃斯基維爾認為,非暴力戰略是唯一正確的方針——「貧困引起恐怖行為,恐怖行為加重貧困。把暴力作為手段,只會摧毀人們最初想要達到的目的。」這一箴言,同樣適用於劇變前夕的中國。
惟有非暴力才能締造新文明。楊佳的悲劇不該重演,更不該複製。中共的軍隊在「六四」殺人,與楊佳闖入警局殺警察,本質上都是殺人。劉曉波入獄之後,中國社會的殺戮之氣越發濃烈,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浙江溫州的民選村主任錢雲會,因反對官方圈地被故意設置的車禍謀殺;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六日,江西撫州發生連環爆炸案,造成三人死亡,肇事者為被政府侵佔土地的農民錢明奇,亦在爆炸中身亡。
從錢雲會到錢明奇,從被殺到殺人,從浙江到江西,時間間隔僅半年。有輿論認為,此事件標誌著中國社會已經從「自焚」式的抗議,轉變為暴力的攻擊,社會進入全面危機時期。很多民眾希望政府儘快從體制上改變現狀,讓民眾可以自由表達思想,政府權力受到有效約束。換言之,若能早日接受《零八憲章》之建議,聽取劉曉波之呼籲,這些悲劇完全是可以避免的。
就連失去孩子的「天安門母親」們都能忍受著心靈的劇痛多次聲明:「我們是公民,而不是怨民!我們必須放棄中國歷史上『以暴制暴,以暴易暴』的抗爭;作為一個有著尊嚴與自信的公民,我們應該加入到世界上為爭取自由、民主、人權而鬥爭的行列。」那麼,劉曉波所堅持的非暴力的觀念,應當成為轉型期中國民間社會的首要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