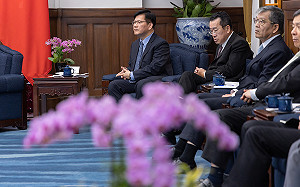台灣,真的是全世界詐騙成本最低的國家。對於最先曝光的車手,社會各界(尤其媒體)用「獵女巫」的心態在追殺;但原本應該是為普羅大眾把關,具有專業地位與學術能力的名人,卻淪為詐騙集團的門神,事發後有的切割、有的神隱,也有的置身事外。鄉民們,認清一個事實吧!對於台灣史,有時《壹週刊》的可信度,還超過中研院台史所與遠流台灣館叢書吧?
2015年上映的台灣紀錄片《灣生回家》,將1895年至1946年間在台出生的日本(內地)人,包括日台通婚者所生下之子女視為「灣生」。其實對於我們這些台文所的學生來說,用出生地與父母的身分來區分是否為灣生,意義反而不大。青少年時代在日治時期的台灣待過,能用文學作品呈現台灣史實的作家,例如寫《台灣縱貫鐵路》西川滿、《陳夫人》庄司本一與《南方移民村》濱田隼雄,才是我們印象中的灣生。
二戰結束前日本在亞洲各地的殖民地,有些即使尚未軍事占領前,就已經有日本移民進入;不過最重要也經營最深、最久的,應該還是滿州、朝鮮與台灣這三地。因此在討論灣生這話題時,與其去對比灣吏(來台任職的日本官員)或灣辯(來台從業的日本律師),遠不如對比其他殖民地裡的日本人,尤其是對比滿生或朝生才更恰當。
從鄉民角度來看,灣生與滿生、朝生一樣,在戰後要被引揚(遣返),但台灣不像滿州,沒有蘇聯共產勢力入侵的干擾,以致在戰火摧殘下治安混亂;也沒有朝鮮那樣的獨立運動與民族對立,除少數地區有針對個別日本警察的報復行動,例如高雄州特高課長仲井清一,被綁架到半屏山圍毆凌遲後再槍殺外,並沒有像滿州朝鮮那樣出現移民村遭屠戮的慘劇。
另一方面日本戰後經濟蕭條,缺油缺糧讓灣生們更想續留台灣;但礙於國府的政策,即使主動放棄日籍,甚至改成漢名,最後也只有極少數國府非用不可的人以外,其他全都必須遣返。灣生被迫返回日本居住後,與滿生朝生相比,最難適應的就是氣候。不過灣生的父母較多來自九州甚至琉球,雖有氣候因素,但其實也沒這麼嚴重。比起滿生與朝生,戰後的灣生幸福多了。
灣生與滿生最大的差異就在於對當地語言的嫻熟度,在政治上918事變後關東軍扶植的滿洲國,不被國際聯盟調查團接受,表面上日本必須與滿洲國建立平等的邦交,因此在滿州的日本孩子也要學華語,以標榜滿漢和朝蒙的五族協和、王道樂土。另一方面華語跟漢字的結合度比台語高,學了之後能閱讀更多書報(日本傳統上流社會就以通漢學為時尚),也更具商機,滿生學習華語的意願自然較高。
至於滿洲國成立前最有名的滿生,就是影歌雙棲紅星李香蘭(山口淑子),她甚至可以冒充中國人多年而不被識破,如果不是戰後抓漢奸時為了保命才交代國籍,誰會相信她不是中國人?
但田中實加虛構的灣生外婆,不但會說台語,與管家夫婦三人在家中還都用台語,這跟台灣人經驗裡內地人讀小學,本島人讀公學校;除少數台籍菁英家庭的子女,有機會在小學校裡與灣生成為同學,最後變成「國語家庭」。灣生用台語交談,就成了最大的破綻。即使在《灣生回家》紀錄片裡,就算如導演所說,都是真的灣生,也都這麼愛台灣,但他們在劇中仍無法像田中實加所虛構的灣生外婆,說出一口流利的台語,然而滿生會說華語的就多了。
先父多年前去北海道旅遊時,接待他的旅館主人就是滿生,她的兒子是在文革後才回到日本,華語說的還比日語好,見到說華語的客人還特別高興。但她的兒子還算幸運,有母親教他日語。很多日本父母甚至為了逃難,拋棄了襁褓中的幼兒,這些被中國家庭收養的戰後孤兒,剛回日本時連50音都不識,最後就只能淪為跟華裔黑幫廝混。
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為了獎勵日人移民台灣,政策設計上可謂無微不至,移民村裡的廁所甚至還有沖水設備,羨煞了來參訪的關東軍代表。當然為幾千人蓋廁所,跟為一百多萬人蓋廁所,難度是不一樣的。
可惜因為水土不服、衛生條件太差、耕種作物選擇、移民無法取得所有權等限制,台灣的日本農業移民村並不成功。1945年遣送回日國的日本人,對照台灣二十多個農業移民村,每村最多也只有一千多人,遠少於遷往於各大都會區或自主移民的日本人。這些移民村的農民,比起在台灣其他的日本人,經濟上與地位上都顯弱勢;但在共享內地人對殖民地人的優越心態上,仍是無可避免的。
田中實加最荒謬的是要將滿生(尤其是戰後孤兒或遺華日僑)的不幸,跳接到她自己想像的灣生上面,要搞一本山寨版的《大地之子》,但她的史學能力又無法駕馭這題材。
滿生的悲劇是在於1945年8月,日本在遭受美軍兩顆原子彈轟炸後,蘇聯紅軍片面撕毀互不侵犯協定,攻入中國東北後,關東軍的精壯都已調至南洋,軍力空虛下就直接徵召開拓團的所有男性,僅留老弱婦孺們,被迫緊急撤退,向有船能回日本的大連、丹東等港口集結,期望有機會能乘船回國。
溥儀宣布退位後的滿洲國裡,上百萬的日本難民,有些婦女帶著幼兒,為了逃避蘇聯紅軍的姦辱,只好改嫁中國人,就像先父在北海道遇見的那位滿生。1950年日本政府對滯留中國的日本人統計是26,492人,1959年就將她們宣告為戰時死亡,對家人發放30,000元弔慰金,並取消其戶籍。
1972年中日建交後,日本厚生省將戰後被中國人收養,且未滿13歲的日本人定義為遺孤,發給他們日本國籍並援助他們回國;但13歲以上的「殘留婦女」則視為自願留在中國,仍然無法回到日本。這些日本遺華婦女在歷經蘇聯紅軍的入侵姦辱、國共激烈的圍城內戰、新中國建立後的清算鬥爭到血腥文革,確實會有裝啞巴的動機與需要;但田中實加要把啞巴嬸的故事搬來台灣,這種灑狗血的劇情,就需要更透徹的史學素養來營造。
1985年日本厚生省制定了遺華日僑的身份擔保人制度,規定她們必須徵得日本親族同意才可以在日本居留,但很多婦女找不到親族擔保人,因此仍然無法回國。1989年日本國會通過入境管理及難民認定法,限制遺華日僑歸國時,只有與日本人有血緣關係的嫡子才能一同取得國籍,養子、繼子則被排除在外。因此有十位不符合規定的殘留婦女,到了日本機場就被扣留,引發日本國民的關注和不滿。
日本政府在民意壓力下,1993年終於取消了殘留婦女與遺孤的差別政策,所謂的啞巴嬸才全數得以回國。但由於遺華日僑長期在中國生活,思想和價值觀都受了影響,又無法嫻熟使用日語,喪失了勞動能力,只能領政府的救濟金維生。加上他們在戰後經濟起飛那段時間不在日本,沒有保險,如今也只能領最基本的年金,成了比「下流老人」更慘的老人。
田中吹得全台醉,錯把滿生當灣生。只要政治正確,這麼荒謬的21世紀《南海血書》,照樣風靡全台;對喜歡台灣史的鄉民來說,真是千金難買的一堂課。但對台灣這「只打童乩卻放任桌頭」的偽善社會,灣騙回家的故事絕不會是最後一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