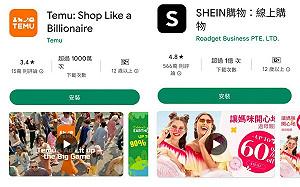余英時先生獲得首屆唐獎之漢學獎,本來是一件實至名歸的好事。就像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讓諾獎增色不少一樣;余英時獲得唐獎,讓初創的唐獎備受世人矚目。
然而,頒獎方和余先生的幾個已經熬成台灣學界名流的學生,心胸狹窄、眼界蹇迫,拼命要將余先生「去政治化」,標榜所謂「純學術」,反倒營造出台灣資深媒體人李蔚所説的「余英時都不余英時了「的荒誕效果。
在記者會上,唐獎的執行長陳振川拒絕回答「余英時教授近來對很多政治事件發表意見,我想問這和他思想的關聯性?」這個問題,評委之一的丁邦新教授更是板著臉回答:「唐獎不考慮政治,我們純就學術論學術。」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長黃建興是余英時的學生,認為余英時一方面像傳統士大夫,批評政治權威,但卻又學習西方公共知識分子的客觀態度,謹守分寸不涉入政治。
這些言行,簡直就是赤膊上陣,將余先生削足適履。倘若唐獎的價值立場真是如此,那麽唐獎根本配不上余先生。
余英時不喜歡「知識分子」這個詞語,認為「知識」一旦成為「分子」,就如同毛澤東所説的「毛」只能附着於「皮」之上那樣,失去最寶貴的獨立性。所以,余英 時用「知識人」這個概念取代「知識分子」,就是要恢復其「雖千萬人,吾往矣」的人格魅力和精神向度。
在余英時看來,知識人當然也是政治人,知識人可以用議政的方式介入政治,發揮對社會正面的影響力。無論是痛斥共產黨軍隊「六四」血腥屠城的慘劇,還是成立 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幫助流亡的中國知識分子和學生領袖;無論是梳理「光棍」毛澤東與中國傳統的關係,還是爲劉曉波的自由而大聲疾呼;無論是批判旺中媒體違背新聞自由的基本原則,還是挺身而出聲援太陽花學運,余先生在這些大是大非的事件中,從來都態度鮮明,絕不含糊其詞。這些言行不都是在參與政治嗎?
同時,余先生對中共暴政的批判,並非如丁邦新教授所言,是始於對「六四」的不滿。七十年代中期,余英時作為美國史學會訪問團的成員,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訪問中國。在那段行程中,他已觀察到鐵幕背後的中國的種種不堪景象。更早,余英時在解讀前輩學人陳寅恪的詩詞時,就發現了中共暴政對知識人心靈的戕害。中共視自由爲天敵,知識人視自由爲空氣和水一般寶貴,因此中共與知識人的衝突不可避免。
余英時支持太陽花學運,引起國民黨保守派的不滿,就連一些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也辱罵其「由學術大師淪為智障人士」。余英時從來不怕因參與政治而損害自己的「學術聲譽」,那麽,唐獎方面以及「余門弟子」們,究竟怕什麽呢?
作者:余杰(中國旅美獨立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