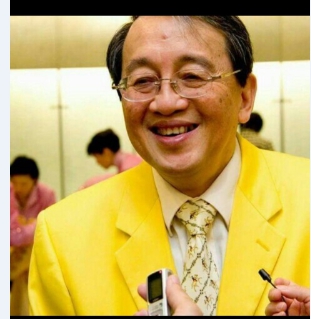善化慶安宮
(善化當時叫「目加溜灣」,慶安宮原址應是當時學校。)

善化老街荷蘭井
(位於慶安宮外,是荷蘭人在一六三六年為了提供飲水給學堂的學生而開鑿的。)
「斌官背叛VOC,捲款逃到國姓爺那邊去了!」
一六五九年的聖誕假期,來自大員的客人帶來了這個勁爆的消息。
客人是小托瑪士及威廉兩位佩得爾家的兄弟。他們跟著瑪利婭的姊姊海倫,姊夫商務助理范˙畢爾賀,大妹漢妮卡及大妹婿下席商務員范˙弗斯登,自大員前來麻豆社渡假。
威廉˙佩得爾自小就在何斌家穿梭不停。何斌的爸爸生前曾抱過他,還給他一個純金戒指當滿月禮物,何斌家的子姪輩也都是他的玩伴。威廉之所以會說大員漢人所用的福建話,就是這樣學起來的。他一向幾乎是把何斌看成「叔叔」或「前輩」。因此,他最是感慨。
而像亨布魯克一家人在福爾摩沙也十年以上了,他們也目睹了歷代大員荷蘭長官對何斌的信任。歷任長官也許有些彼此不是互相對味,像維堡與揆一,但他們全都非常倚重何斌,也禮遇何斌。因此,何斌的叛逃,讓VOC上下都非常心寒。
小托瑪士說:「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啊!」
亨布魯克說:「先別這樣驟下結論,何斌這樣子走法,把家當都捨棄了,一定也有他的苦衷。何況在他走之前,也被監禁看管論罪的。狗急跳牆,何況是人。他是否遭受了什麼委屈呢?威廉,你有沒有知道什麼內情?」亨布魯克知道威廉和何斌關係較密切,就指名威廉把全部來龍去脈說清楚。
范˙弗斯登不服氣的插嘴:「斌官確是捲款逃走。苦主除了VOC外,大員市的漢商被騙的也不少。」
威廉支著下巴,有些懶洋洋的說:「這事其實說來話長,也真是有些複雜。」
他啜了一口葡萄酒,又剝了一瓣橘子塞入口裡,叫聲「好酸」,然後才像在回憶一般,慢條斯理的說:「大家可還記得,在凱撒長官任內的最後一年,我記得是一六五六年六月,國姓爺來了一封措詞嚴厲的信,表示要對大員實施貿易封鎖。我之所以記得這麼清楚,是因為斌官在為長官翻譯這封信件時,特別拿給我,要我詳細讀一遍,還問我看懂多少。」
瑪利婭說,「真的?我怎麼不知道?」因為瑪利婭清楚記得,前幾年,她為了學漢人語言去何斌府邸,還見到國姓爺的部爺吳豪,來請大員的荷蘭醫生替他療傷。也還記得更早在威廉的姊姊瑪格麗特和柯來福牧師結婚的婚宴上,那時的凱撒長官還得意揚揚說,這樣表示國姓爺很信任荷蘭人,只要將來國姓爺和大清國達成和解,轉口貿易就可以恢復興旺了。而瑪利婭也知道,一六五七、五八年度,大員商館又因貿易的興旺而獲利大增。例如一六五八年度,支出三十九萬荷盾,收入五十九萬荷盾,總盈餘二十萬荷盾,讓巴達維亞荷蘭總督馬綏掘(Joan Maetsuycker)非常高興。
亨布魯克牧師最近已續約,再留福爾摩沙。續約後和媽媽去了一趟巴達維亞作教會交流,方才回來麻豆社。而爸爸決定續約,有一部分也是因為大員的貿易又欣欣向榮,讓爸爸覺得對福爾摩沙有信心。因此,她不清楚,在她心情最低落的一六五五及一六五六,大員與國姓爺的通商關係也同時陷入低潮,也不知原來鄭荷之間這幾年有這麼多波折。
威廉還來不及回答,她又問:「我還以為我們和國姓爺一直保持很好的關係呢。那麼,在一六五六年,為什麼國姓爺對我們的大員商館實施斷航禁運呢?」
瑪利婭的妹婿范˙弗斯登是下級商務員,插嘴說,「這些商業上的事我比較了解,就讓我來從頭說明吧!」
「這事要自更早的一六五五年說起。一六五五年七月,國姓爺寫信給凱撒長官,抱怨說馬尼拉對他的船隊很不友善,殺他的船員,奪他的船貨。國姓爺說,他屢次交涉,未獲改善。西班牙人或強奪貨物不付款,或不按約定價格,隨意丟了一些錢充數了事。國姓爺的結論是,他實在已經忍無可忍,不能讓他自己和他的善良同胞,被西班牙人這樣欺凌。因此他下令禁止並封鎖所有漢人船隻到馬尼拉,並寫信來要求大員的荷蘭人也配合。」
「凱撒長官當時回信說,荷蘭與西班牙已經恢復和平,不再敵對。因此,抱歉,不能這樣做。」
「過了兩個月,國姓爺又來了一封信。這封信是寫給何斌和大員所有漢人頭家,再由他們轉告大員長官凱撒。國姓爺說,新任的巴達維亞總督對他很不友善,他的船隊在巴達維亞備受刁難。巴達維亞想獨占利益,不准他的船去滿剌加(註一)、柔佛和彭亨。而且不只如此,國姓爺有一艘去舊港(註二)的船,被搶走四百担胡椒,讓他蒙受巨大損失。國姓爺說,他鄭重警告,如果不能有所改善,大員商館就要為一切後果負責。」
范˙弗斯登回憶著,「他說,如果他的船再受到刁難,他將不再相信他與荷蘭之間的友誼。他將發布公告,禁止所有漢人船隻前來大員或福爾摩沙的任何港口。無論什麼藉口,都不許任何船隻運貨來此,或來此取貨。」
小威廉插嘴道:「我還清楚記得國姓爺的用語」。然後他作勢一字一字地唸出:「他說『我的話就像礫石中的黃金。我所說的,必將實施。』」(註三)
范˙弗斯登繼續說:「在同一封信,國姓爺也用很嚴厲的口氣命令大員漢人,要他們遵守他發布對馬尼拉的貿易禁令。」
「斌官和大員的漢人頭家們一收到這封信,立刻翻譯,並轉呈大員長官和巴達維亞總督。」
范˙弗斯登滔滔不絕地說:「凱撒長官輕描淡寫回應說,大員的商人也不喜歡去馬尼拉,因為馬尼拉確實有欠款的行為。但是依照條約,荷蘭人和西班牙人仍是朋友。至於國姓爺寄來的命令大員的漢人商人對馬尼拉的禁運公告,大員當局決定不予公佈,因為這對公司與荷蘭人會造成主權損害。」
范˙弗斯登停了一下,眼光向眾人巡視了一遍。「而巴達維亞更是打馬虎眼,僅說『查無此事』,而不予理會,擺明不予配合。」
瑪利婭接口說:「巴達維亞這樣也太過分了,那就不能全怪國姓爺。」
范˙弗斯登把一杯啤酒一飲而盡說:「威廉,那以後的部份,由你來說吧!」
威廉瞄了瑪利婭一眼,接下去說:「後來,就是第二年,我剛剛提到的一六五六年六月底那一封對大員公司全面禁運的信了。那一封國姓爺的信,在斌官翻譯成荷文時,我也加入一些意見,使措詞用字更為精準。國姓爺的信常是長篇大論,鉅細靡遺,卻又措詞有力,語意明確。又看來有條有理,絕不模稜兩可。而他做決策,既果斷有魄力,又周全細膩,令人覺得義理人情兼顧,是個很厲害的對手。」
威廉˙佩得爾的聲音很高昂,帶著手勢:「我記得很清楚,在那封宣佈對大員禁運的信中,他對大員的所有漢人發出三點命令。」
「首先,他宣佈要對我們大員貿易制裁,又理直氣壯列舉了許多禁運理由,好像道理全在他那邊。」
「接著,他又故示寬大,訂下一百天緩衝過渡期,表示允許在他地的船隻有充裕時間在期限內歸航。等到屆限一到,就嚴格執行禁航。連可以或不可以帶回什麼貨品,都寫得清清楚楚。」
「第三點,再強硬宣示,犯禁的漢人,貨品沒收,人員一律處死,決不寬貸。」
威廉˙佩得爾愈說愈激昂:「這一封信,讓我們的荷蘭長官及評議會最受不了的是,信的對象針對著在福爾摩沙的每一位漢人,擺明了公然侵犯我們荷蘭人在福爾摩沙的管轄權,完全不把我們放在眼裡。但問題是,他的抗議相當有理,讓我們無法反駁。但他的手法實在太厲害,不論是福爾摩沙還是其他港口的漢人船隻,都不敢違背他的命令,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
商務員范˙弗斯登點點頭,接下去說:「是的,公司最無法忍受的是,國姓爺幾乎把大員、全福爾摩沙,甚至包括馬尼拉、巴達維亞的漢人,都看成是在他統治下的子民。」
商務員繼續說:「他還真的說到做到。在大員及福建間往來的船隻,自當月來四十八艘,去四十七艘。下個月即銳減為來五艘,去十九艘。再下個月時只剩來一艘,去八艘。之後,也就是一六五六年九月,迄一六五七年夏季一整年,大員及福建兩地間未見一艘往返船隻,完全斷絕。」
「那些平常聽VOC的命令,居住在福爾摩沙的漢人商人,都陷入困境。」
在旁邊聽了很久的小托瑪士˙佩得爾這時也開口了:「國姓爺的執行力確實很可怕。所以他的軍隊能以少敵多,讓韃靼的軍隊就是贏不了他。聽說他令出必行,處罰嚴格,親疏不計,這一點Christian Beyer當年就領教過了。」小托瑪士把手一攤,說:「拜爾醫生當年去廈門替他醫病,卻不時看到他動不動就殺兵士,殺將領,甚至殺自己的侍僕,嚇得他不敢久留,趕快跑回大員。」
范˙弗斯登繼續他原先的話題:「然後,就是一六五七年九月及十月的幾個大颱風,讓整個福爾摩沙好像泡在水裡,不但死了近千人,房子倒塌,糧倉浸水,糟糕的是稻米和蔗糖的收成也大受影響,大員公司遭受到前所未有的財政困境。於是這一年十二月,揆一以議長的身份,接任了VOC在福爾摩沙的長官的位置。凱撒這一任,可說運氣不佳,又是蝗災,又是水災,人際關係也不順,真是做得灰頭土臉。」
註一:今麻六甲。
註二:今蘇門答臘巨港。
註三:中文可能是「金石良言,言出必行」。(中研院翁佳音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