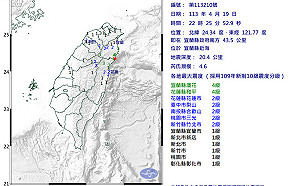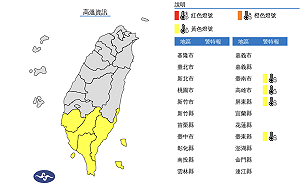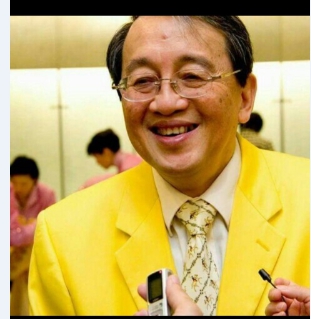漢辦撕書與胯下之辱——兼論朱雲漢媚共之下場 (作者原標題)
當中國變得財大氣粗之後,拍馬屁、抱馬腿者爭先恐後,中共豢養的多如牛毛的御用文人自不必說,在中共的統治範圍之外,此類人物亦數不勝數,如德國前總理施密特、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花旗銀行董事庫恩、美國霍普金斯基金會中國部主任李成、香港影星成龍和溫兆倫等等,這個聲名顯赫的「人渣榜」越來越長了。台灣學者(學閥?)朱雲漢亦使盡渾身解數,擠了進去,佔有了一席之地,終於可以分享這場「人肉的盛宴」了。
然而,平地一聲驚雷,剛剛與北京進入「蜜月期」的朱雲漢,在中國漢辦撕書事件中一下子被打回了原型,不得不承受了一次胯下之辱:二零一四年七月,在葡萄牙舉行的歐洲漢學學會第二十屆雙年會的開幕典禮上,中國國家漢辦主任許琳要求主辦方將會議手冊上第五十九頁有關蔣經國基金會贊助部分全部撕掉。要求不果,許主任遂作河東獅吼,親自率領一群嘍囉動手撕書。這群撕書者沒有留意到,蔣經國基金會的執行長是大名鼎鼎的朱雲漢,而朱雲漢是近年來關於「中國模式」的最為忠心耿耿的鼓吹者。難道這是一場「大水沖了龍王廟」的「美麗的誤會」?
朱雲漢為何譴責中國「未能融入世界主流」?
「漢辦撕書」事件發生之後,台灣外交部提出嚴正抗議,歐洲漢學會亦發信譴責此一破壞學術自由之舉。就連中國國內的網絡輿論,也大都對此種粗暴野蠻的舉動不以為然、冷嘲熱諷。納粹焚書,中共撕書,可謂交相輝映。納粹德國的結局一目了然,共產中國的未來會陽光燦爛嗎?
一如既往,中共黨報《人民日報》旗下的法西斯黃色小報《環球時報》,隨即發表社論力挺「漢辦撕書」。這篇題為《漢辦主任在國際會議「撕書「不丟人!》的社論,大概出自於「一號五毛」胡錫進之手。
社論首先攻擊台灣方面的「小動作」——「隨著大陸的實力和國際影響力與日俱增,臺灣的國際空間一再被壓縮,臺灣需要做的是認清大勢,主動順應,為推動兩岸統一做出貢獻。但遺憾的是,臺灣方面總是既近視又遠視,就是不願意面對現實,喜歡搞一些小動作,比如在國際會議上鑽營,獲得點臺灣的國際存在感,這越來越無聊,也越來越沒用了。」然後將撕書升級到愛國的高度上:「任何懷著愛國心的中國人,遇到這樣的事,都很難坦然處之,這不是某個人的私利,而是國家大義。國家漢辦作為參會方,對這樣的事沒有回應,不做質詢,那才是失策。『撕書』是一種簡單明瞭的方式,表現出堅決的態度。」既然撕書是向黨國表忠心,誰還幹說三道四?
這一次,中共不顧朱雲漢多年來在海外幫助其拓展「軟實力」所效之犬馬之勞,毫不留情地給了他一記響亮的耳光。朱雲漢痛徹肺腑,無法保持沉默,破天荒地接受與之價值觀迥異的《自由時報》記者鄒景雯之專訪。在題為《政治箝制學術,中國在歐洲漢學界栽跟頭》的報導中,朱雲漢分析說,過去這十年,中國官方發現不能高舉著官方馬列主義、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回過頭去把孔子、傳統的東西搬出來。」但他們在具體做法上,仍然在其官僚體系的思維下,中國大陸的教育部,對於他們的大學,也許像台灣三十年前,是非常清楚的指揮與階層關係,大學校長聽命部長,院長聽命校長。這次的錯誤,表現了他的習性,體制就是這個樣子,在國內頤指氣使的指揮那些學者,到國外就不自覺的以為可以比照。到今天,他們還沒有真正去融入世界的主流。」
朱雲漢批評說,中國大陸的做法,綁上許多意識形態或外交目的,反而得不到先進國家學術主流的認可,也會扼殺學術本有的活力與創造性。「在他們自己國內就應該做很多的改變,不能老用政治箝制學術。這次栽了一個跟頭,在歐洲造成群情激憤,一次就消耗掉了過去長期的經營,他們應該會有些學習吧。」挨了中共的耳光之後,朱雲漢似乎稍有覺醒,終於承認存在著超越於國家和民族之上的世界主流、普世價值。而學術的自由和獨立,也包含在世界主流和普世價值的範疇之內。
朱雲漢為何讚美中國「不必融入世界主流」?
然而,翻檢朱氏此前一以貫之的觀點和論述,他是「中國模式」在台灣最不遺餘力的吹鼓手。朱雲漢曾在台灣大學作過一場名為《中國大陸興起與全球政治經濟秩序重組》的演講,真是「滿口荒唐言,一筆糊塗賬」,玷汙了臺大作為台灣最高學府的聲譽。
在演講中,朱雲漢斬釘截鐵地宣稱:中國模式在全世界的意識形態版圖上,在美國式資本主義和西歐式民主社會主義(福利國家)體制以外,開創出了第三條道路。「它會逼著第三世界所有國家的政治精英重新去思考,怎麼樣去平衡正當程式、維持國家治理能力、取得最好發展結果,應該用什麼樣有效的制度、安排和策略來追求它們之間的平衡。」將朱雲漢的前後言論逐一對照,可謂自相矛盾、破綻百出。
朱雲漢認為,中國經濟的崛起得益於中國的政治體制。「中國共產黨這個體制摸索奮鬥三十年,這三十年並沒有白費。很多人以為中國一九四九年到改革開放三十年都浪費掉了,是完全黑暗時期。這個認知本身就是錯誤的。中國這個時期以高昂的社會代價——很多人因此而犧牲——去建構了改革開放的基礎。……另外,中國完成了一場相當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因為它把私有財產權,尤其是最重要的土地資本集體化,不是國有就是集體所有。而這個龐大的集體資產,大部分是國有資產,是中國後來三十年快速發展的資本。」
這段論述是為習近平的「前三十年與後三十年和諧統一」的觀點背書。此種辯護詞可以原封不動地套用到納粹德國頭上:如果不是希特勒匆忙發動對外戰爭,納粹當年的經濟發展才是讓中國望塵莫及的奇跡呢。當年,納粹德國的工人就有甲殼蟲汽車開,也有條件優良的療養院住;今天,中國的農民工和下崗工人卻宛如現代奴隸,或開胸驗肺、或跳樓自殺。如果你是一介平民,你願意生活在哪個時代,那個國家?
這段論述中最無恥、最冷血的部分是:朱雲漢用「很多人因此而犧牲」一筆帶過共產黨政權用暴力奪去數千萬民眾生命的這一事實。在中共的統治下,許多人在和平年代死於比納粹屠殺猶太人的種族屠殺更慘烈的「階級屠殺」,許多人在「風調雨順」的三年中死於中共人為製造的大飢荒。若非朱雲漢的長輩逃亡到台灣,恐怕早已淪為孤魂野鬼,哪裡輪得到他在此胡說八道?而中共以「分田地」為名獲得農民的支持,從而打敗國民黨;但一旦奪取政權,立即又從農民手中奪走土地。這是以國家的名義實施的巧取豪奪,在朱雲漢眼中,居然成了一種理所當然的、優良的發展方式。
接著,朱雲漢又對後三十年的中國塗脂抹粉。「最突出的設計是一黨專政。這個體制看起來和世界潮流有點格格不入,但它的重點在於一黨專政如何維持政治穩定和治理能力。這裡面有幾個值得注意的地方。一個是它解決了繼承危機問題和個人獨裁的問題。中國大陸建立了一些制度去克服這兩個問題,一個是任期制,一個是接班制。這一體制解決了個人獨裁問題,貫徹集體領導。政治局常委就像非常強勢的總統——這個總統是由九個人一起做。下一屆政治局常委可能是由七個人一起做。各自有各自的分工,但最重要的決定要尋求共識。」
所謂「集體總統制」,其實是中共御用學者胡鞍鋼對胡錦濤時代不得以的、「寡頭共治」的統治方式的概括,朱雲漢掠人之「美」而不加註釋,不是剽竊又是什麽?其實,「集體總統制」並未定型,只是由胡錦濤的弱勢地位而衍生出的暫時局面。習近平剛一接班,便自我加冕為「紅朝皇帝」,設立多個小組並自任組長,大亂原有的權力格局,一個人集十四個重要頭銜於一身,成為毛之後最有實權的中共黨魁。」習式變法「將胡錦濤實行了十年的「集體總統制「一舉摧毀,將政治局變成如奴僕般為其個人服務的軍機處,個人獨裁再度成為事實。
而「周永康、薄熙來、徐才厚、令計劃「這「新四人幫」的垮臺,顯然不因為腐敗,而是因為要搶班奪權。這種你死我活、血肉橫飛、赤裸裸的權力鬥爭,顯示中國的權力交替並未形成一種文明、穩固的「定制」。沒有多黨競爭和全民選舉,權力的交接永遠不可能以穩定與和平的方式完成。中共政權連黨內的權力分配都不能順利達成,對社會的控制又怎能如臂使指呢?如今的中國,烽煙四起、民怨沸騰,所謂「穩定壓倒一切」,每年耗資七千億人民幣來「暴力維穩」,才勉強維持,這難道是一項光榮而美好的經驗嗎?哪個第三世界國家願意學習呢?
反共就是反對「不文明」的暴政
濫用台灣的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為中共的專制、獨裁、暴政張目的朱雲漢,居然混成了台大教授和中研院院士,並執掌蔣經國基金會的龐大資源,可見「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可見台灣社會尚未建立起對民主、自由、人權、憲政的普世價值的充分認同和尊重。
很多台灣朋友說,太陽花學運如同一面照妖鏡,照出了人與妖之別。果然,太陽花學運期間,朱雲漢在《天下》雜誌第五百四十四期發表「台灣離民主崩壞還有多遠?」一文,質疑「為何少數抗議學生,可以強制阻撓由一千六百多萬合格選民選出的立法委員正常行使憲法職權」。當然,他不會質疑執政黨的立法委員為何敢於在三十秒內強行通過自取滅亡的「服貿協定」,而只會如同蜀犬吠日那樣對覺醒的公民社會氣勢洶洶地叫囂。
朱雲漢熱愛共產黨的獨裁暴政,自然對從「反共」到「媚共」一夜變臉的國民黨政權傾心支持。他執掌蔣經國基金會龐大的資金,縱橫學界、締結朋黨,成為不可一世的學閥。殊不知,該基金會既然以「蔣經國「冠名,就當遵循蔣經國之訓導。對於彼岸的共產黨,蔣經國說過兩句最經典的話——「我們在任何情況下都絕不會同中國共產黨進行任何形式的談判,我們過去的經驗已使我們有了足夠教訓,無論如何不能相信共產黨人。」「只有在中國大陸的人民擺脫共產主義時,我們才會坐下來同任何人談判。」朱雲漢既已經背棄蔣經國所奉行的原則,為什麼不「毅然」辭去蔣經國基金會執行長的職務呢?
中共政權從來都是薄情寡義,無論你如何拱衛和諂媚,它照樣要你接受胯下之辱——如此才能證明你百分之百對它服服帖帖。《環球時報》引以為傲的「漢辦撕書」,在任何一個文明人眼中,都是一件不文明、反文明的行為,就連朱雲漢這個媚共先鋒都忍無可忍了。撕書不文明,那麽六四殺人呢?這樣一個既撕書又殺人的政權,這樣一個殺死孩子不許母親哭泣的政權,不管你身在何方,豈能不挺身反對?如今,香港已經被吞噬,台灣亦危在旦夕。竭澤而漁、易子而食的「中國模式」,不僅奴役十三億的中國民眾,而且對外輸出、危害全球,有識之士豈能坐以待斃,無所作為?
近日,王丹在《蘋果日報》發表一篇題為《有些事情,事關文明》的文章。王丹說:「我從來不諱言,我的政治立場是反共的。」當年,兩蔣時代的台灣,「反共」為國民黨的統治提供意識形態的支援,反共是可以封妻蔭子的好事。那麽,在今天這個「反共」不再時髦,唯有「媚共」才能陞官發財的時代裡,王丹為何還要「選擇這個很老派的政治立場」?
王丹的回答是:「不錯,中共很強大,也帶動了經濟增長,但是同時,這個政權的某些做法完全是與人類社會經歷幾百幾千年,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文明規範背道而馳;更為嚴重的是,他們依仗著他們的強大,迫使太多的國家,太多的政客,太多的人,對於他們這種破壞基本文明的行為裝聾作啞,淪為共犯。這樣的中共,是在用暴力強迫人類社會跟它一起在文明的海面上向下沉淪。只要是對自由稍微有一些文明期許的人,有什麼立場不去反共嗎?」毫無疑問,反共也是我一以貫之的立場,即便這是一段孤獨的、少有人走的路,我亦風雨兼程、無怨無悔。
而聰明絕頂的朱雲漢,究竟是唾面自乾、繼續當中共的走狗,還是洗心革面、站起來做人呢?
作者:余杰(中國旅美獨立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