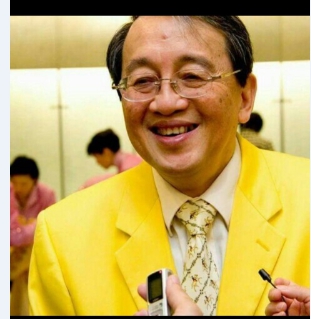文學是生命感覺具體放射,以想像把生活經驗重整出新的光芒,其內涵就是生命價值的探索。與其他藝術媒介之不同,它是用字的。
文書表達、報導表達是紀錄表達;但是文學表達卻提昇為創作藝術。除了科學發明是一種創作有跡可循外,文學創作因把夢與經驗互燃的神秘叫作靈感,常讓人誤解為想幻不實,無益經濟;事實上,這是以膚淺的流俗作品來誤解深刻的文學藝術,遂以之形成對人文的輕忽。
比如,現實生活上,鄭捷殺人的可怖或恐攻陌生人的殘謬早就超過一般心理學能夠了解的範疇。但在二十世紀前半葉,法國作家卡缪卻早已寫出了《異鄉人》,當人異化了自己,也異化了別人的存在,一切陌生價值顛倒,冷漠層越來越強時,當然是可以為一點不快的累積,突然殺人的。
通過這樣文學的感同身受深刻的描寫,我們也發現自己非理性的一面,也由於這發現,我們溶化了殺人的衝動,使成更深反省的泥土。這就是文學創作的價值與貢獻。
可惜,由於科技與經濟的發達,知識的橫流往往遮蓋生命感覺,遂使知識化與管理化成為社會主流,倒也罷了,更誤解了文學藝術的本質,使文學跌成知識化的尷尬角色。不少文學研究著作都以貌似客觀的「文學知識」,如某某主義,某某意識,某某同性戀異性戀如何又如何,甚至也有以「陰莖意象」這樣缺少美學的粗糙為題的。如此失去生命感覺,難怪無感又無解的讀者只有退避三舍,也對於依據「文學知識」寫出來的作品之得獎,更感不解。
當這類以「文學知識」為主的博士教授幾乎佔滿學院時,形成一個生態,自然排擠文學創作者進入學院帶給學生創作活力的機會,甚至排擠有真才實學卻無博士學位的老師。我們的博士學位與升等論文要求,確實已淪為工廠管理方便辦法了。
讀了東華大學教授許又方先生大作〈文學作品不能升等嗎〉直指其他學科皆可有取代研究論文的活潑辦法,唯文學作品不行的荒謬性。許先生快人直話,卻刺穿了文學系研究與教育的問題,若能解除這盲點,讓作品活源流入僵化知識化的文學系研究與教學裡,同時也引進作家通過推薦遴選可以直接任教,等同教授的制度,溶解冰箱生態死結的文學系變質,才是誠懇與無辜的師生之福,當然也會對文化與出版困境有正面活潑的貢獻。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