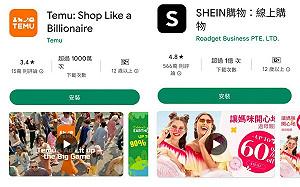沒有一種武器比裸奔,更赤裸裸、更震撼。全民應該裸奔上街,要求政府給納稅人赤裸裸的真相與公義,為士官洪仲秋的死追出真相,為被苗栗縣政府強拆大埔民宅的受害者向政府討回最基本的公義。
今年是現代Streaking裸奔40周年。1973年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馬里蘭大學有533位學生集體裸體奔跑,揭開現代裸奔的序幕。自此裸奔常成為一種示威的工具,在文化界與體育圈成為焦點話題與流行,帶動性革命、政治訴求、對女權主義的一種反彈等等效應;如1974年,尼克森陷在「水門事件」的泥沼,有一個人扮演尼克森裸奔,穿上一條粉紅色內褲做為諷刺:太膽小不敢裸奔。
是的,我太膽小不敢裸奔,當我看希臘羅馬的男性雕像,我對自己的身體就自慚形穢;但內心的ego又讓我變的自大。於是我有兩次「偷偷摸摸公然」裸露的經驗,加上引號,是因為我不知我的裸露有幾個人看到。
1970那年夏日的脫光
那是1970與1971年的夏日,我20歲的時候。
1970年的8月我被台北縣政府教育局分發到金山鄉濱北海的中角國小擔任小學老師,當時還沒有「金山核一廠」(1971年底開始施工)金山與三芝之間這段景色優美、保有自然風貌的兩線道濱海路段,客運班車寥寥可數,私家車也不普遍,平日更少行人。8月某天到中角國小報到,那時還是暑假期間,我就跟當地老師,借了一部腳踏車,從中角慢慢騎到石門,沿途覺得好玩就停下來欣賞北海岸的石頭與浪花,另一側翠綠的山坡,甚至還有一道小瀑布從山脊流下來,四下無車無行人,我就放雙手騎在馬路中間,無比輕鬆敞開襯衫衣釦;當年分發到這些只有12班的學校都算是偏遠地區,以我這種相信「霓虹燈比星星動人」的個性,我當時有被流放邊疆的無奈與痛苦;不過那個下午的腳踏車自我行,讓我覺得「我應該試著愛上」這個偏遠之地,雖然在此之前,我也常到金山青年活動中心參加跨校際的社團活動,對基隆到金山這段海岸線十分熟悉,未來我應該多探索金山到三芝這段純樸的北海岸。就如一位老師告訴我:得不到你所愛,就愛你得到的。只是,道理我懂,但做不到。一輩子無知的在追求我的所愛。
在1987年解嚴之前,海岸線都由「警總」控管,穿制服的人隨時注意觀察接近海岸的人,特別是「陌生人」。趁9月初開學前的這幾個星期的空檔,我常穿個便鞋或拖鞋、卡其褲白襯衫,從學校走向中角那一處碉堡,朝金山青年活動中心那個方向的沙灘漫步,站在沙灘上迎海浪襲來;或坐在沙灘閱讀,除了當地放暑假的孩子,沙灘沒甚麼「外地人」。我讓海防哨的士兵「習慣我」這個新來的小學老師。(當年似乎像Davie Lean 1970執導的Ryan's Daughter「雷恩的女兒」的聚落,請不要用2013年的眼光看現代充滿咖啡簡餐、豪無特色的中角)
幾天之後,我認為「他們」已「認識」我,決定脫掉衣服「下海」;我不會游泳,但誰能抵擋夏日的浪花,何況我的學校宿舍只有5分鐘不到的腳程。我慢慢的脫下外衣褲(衛兵沒有過來阻止)放在沙灘上,著一條白色內褲下海,順著沙灘走向寬闊的大海,瞬間自然而然忘掉自己對外表的沒信心,談不上「掙脫」,只覺得心中十分舒服舒暢,肉體解放了,心靈也自由了。只有四角褲角隨波浪漂動被海水灌得鼓鼓的,很累贅不自在,於是自然的脫掉內褲,讓裸露的身軀隨海浪載浮載沉,美呆了;那年我還是處子之身,但我猜想,一位女人柔情似水,而情慾如浪花,我當然赤裸隨她所欲;或者我仿佛在母親的子宮無憂無慮,雖然我們都不記得在媽媽的體內是怎樣的情境。
1971年夏日在營區脫光散步
那年10月我就服役去了,我是空軍預官補給官,我開玩笑我是Air Supple,比洪仲丘百倍萬倍的幸運,在台南大林空軍司令部上下班,軍官宿舍就在辦公室對面,除上班外,下班完全屬於私人時間。宿舍裡住的都是預官,有如大學宿舍,當時我們聽的都是西洋流行音樂與AFNT(美國空軍台灣電台)的節目,有一個寢室的預官總是把西洋流行音樂音量開到最大,雖然吵雜,但也和平共處相安無事,到現在我還是習慣西方的樂曲而且感動不已,我向來不聽所謂的國語歌。
在服預官役這期間我認識不同單位的預官Michael,由於我們喜愛談論國內外時事很投緣而相交至今;1970年代初期是台灣外交最險峻的年代,被趕出聯合國、尼克森訪問大陸,那時國內媒體完全被警總控制,不是不報導就是以最不顯眼、輕描淡寫一下。但我的職務與「美軍顧問室」有關,我在顧問室每天看到空運來台的美國媒體對這些新聞的報導與圖片,下班後與Michael「偷偷」分享,瞬間認知「原來我們的國民黨政府都在矇騙老百姓」,這也是讓我之後決定當記者的主因。
Michael的父親任職於中央信託局,是一位高級公務員;母親曾在台北美軍顧問團工作,他退伍後就一定要到美國留學。他告訴我出國後以後就住在美國了。1972年他終於到美讀書、就業成家。一到美國Michael就幫我訂閱National Geographic(國家地理雜誌,至今40多年我還是這雜誌的讀者),省掉我還得跟政府申請核可辦外匯等「不自由」的程序。如今我們都各自成家立業,他育有一兒一女也都結婚生兒育女了。
1971年夏日的某個晚上,我們都只穿一條內褲,坐在宿舍門外的台階高談闊論,今天我已不記得甚麼原因,或是打賭,是我還是Michael是誰先提起,就脫掉內褲光溜溜的在營區走一段路。於是我們兩人就赤裸裸的在營區的大馬路散步,南部夏日的夜晚涼風習習,說實在的,赤裸裸的吹風是蠻舒服的,特別是下體私秘處。我想應該是沒有人發現有兩個預官赤裸裸的在營區漫遊,否則,不曉得會有怎樣的結果。幾年後我們偶而會在妻小面前十分「自傲」提到這段當年勇,因為我們敢為別人所不敢。但我內心深處:身體是我理念、意志的延伸,戒嚴的政府管不了我的
我是在大白天公然赤裸裸,只是那是在海水裡;也曾赤裸裸的在營區散步,只是那是某年夏日的某個夜晚,有誰看到當年我年少的裸體,看來,只有天曉得。
但,如今年過60,我不怕赤裸裸,只怕傷了別人的眼睛。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