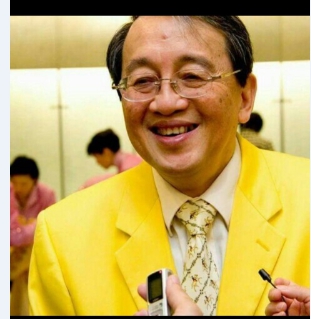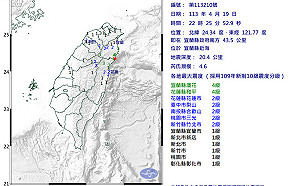大詩人奧登擦過諾貝爾文學獎
不是唸英美文學的人,可能不一定知道這位因堅持說實話而錯失1964年諾貝爾文學奬的美國大詩人。生於英國(1907),後入籍美國(1939),詩人奧登(W. H. Auden)規律的詩節裡語帶超然反諷口吻的風格,引領美國1940年代整個世代的詩風。
喜歡莎士比亞劇作的人多少都知道奧登曾在1946至1947於世界著名左派大學新學院(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講授莎翁全部劇作的盛事,這堂課大受歡迎,每堂約有五百人購票聽講。有高中生每週通勤前往,終身難忘聽奧登的課被啓發興奮的經驗。奧登並未留下講授莎翁全集的稿子,2000年出版的Lectures on Shakespeare主要是根據當時聽課學生Alan Ansen所做的驚人筆記編訂而成。
現代主義名家,舉凡喬哀思、葉慈、艾略特、龐德等,總表現出文化先導與權威者,為其時代與國家擘劃議題的藝術家英雄樣貌。奧登反其道而行。在其藝術領域裡他確實有專業的獨到處,但在其他方面,他認為,他並不比他的讀者強,既無道德權威,也無特別的洞見。
因為這樣的態度,曾有一位因犯竊盜入獄的加拿大受刑人在監獄圖書館閱讀到奧登的詩後寫信給他,他回信了,從此開啓他們之間長期的通信,藉由通信,奧登給這位受刑人上非正式的文學課,而從卡夫卡開始讓奧登感到特別愉快。
給受刑人上卡夫卡的小說,這情境真讓人玩味。奧登專家也是其文學遺產執行者孟德爾頌(Edward Mendelson)日前在紐約時報書評為文“The Secret Auden”敘述奧登不為人知的一面。前段故事就是那位受刑人打電話給他,告訴他這則軼事,至於為什麼以卡夫卡開始讓奧登感到特別愉快,孟德爾頌教授並未說明。
或許與關在監獄的人探討卡夫卡作品裡懲罰與困在制度城堡的意義,可以讓受刑人更能進入其小說世界吧?
低調、為善不欲人知,有俠客之風的奧登留下生前不為文學界、媒體所知,死後經由當事人或其朋友說出來頗具戲劇性的善舉。
有朋友跟奧登說他們一位朋友籌不出錢開刀,於是奧登就請這位需要開刀的朋友一起吃飯,吃完飯要分手前奧登遞給他一本大筆記本,裡面有The Age of Anxiety這本他的書的手稿。後來德州大學買下這個筆記本,他的朋友就有錢開刀了。
他有時看似自私死要錢會讓被煩到的人很不舒服。比方NBC製作轉播《魔笛》,歌劇的歌詞是由他與Chester Kallman合作翻譯,他跑到製作人辦公室,要求立即而非依合約的日期支付支票。他死賴著一直等到支票拿到手的樣子看起來很討厭。幾週後當NBC收到已兌支票,發現支票簽署:支付給Dorothy Day。原來是紐約市消防局要Dorothy Day花大筆錢整修她管理的遊民庇護所,若未依規定的時間花錢整修,庇護所就會遭到關閉的命運。
在文學聚會裡,奧登也會來一招從名人的談話圈圈溜開,跑去跟在場最不起眼的人聊天。一位書信作家在報紙上回憶60年前的一則往事。那天他的英文老師把他從鄉下的文法學校帶到倫敦參加一個文學會議,到了會場,他的老師就把他丟下,找朋友去了。他手腳不知如何擺放孤零地在一個小角落,這時奧登朝他走過來,跟他說:「在場的每個人都像你這麼緊張,只不過他們會虛張聲勢,所以你也必須學學怎麼唬弄。」
幫助貧苦弱小是他的信念,但要他主動說出所做的善事,會讓他很不好意思,所以從來不說。孟德爾頌教授在奧登的文件裡發現數封信裡透露奧登透過歐洲救濟機構贊助兩位二戰遺孤就學到大學畢業,這項善舉持續到他1973年過世,幫助了不少孤兒。
他也提攜不知名的年輕詩人。當這些後進將他們的詩作寄給他,他皆認真看待,給予技巧上細節的建議。
現在來說說他是怎麼擦過諾貝爾文學獎的。由於奧登是同性戀者,他敏感到1961年諾貝爾和平奬瑞典籍聯合國第二任秘書長道格.哈馬赫德(Dag Hammarskjöld,生於1905年)有同性戀傾向。哈馬赫德家學淵源,接續其父親擔任諾貝爾委員會委員,曾任瑞典外交部秘書長與不管部部長,擅長談判,具人道情懷。1961年9月,僅負責維和的聯合國部隊與剛果共和國軍閥在加丹加的軍隊發生衝突,9月18日夜哈馬赫德前往調停,乘坐的道格拉斯DC-6在今尚比亞恩多拉附近墜毀,與他同時殉職的還有15名的陪同和機組人員。
哈馬赫德擔任聯合國秘書長期間在瑞典地位崇高,墜機身亡被追贈諾貝爾和平奬。1964年奧登與Leif Sjöberg合作翻譯哈馬赫德死後出版的著作Markings一書,他在序言提到哈馬赫德對自己的深深迷戀,是同性戀的徵兆,不過這個傾向完全內藏,並未表現於外有實際行動。
哈馬赫德的遺產執行者與友人看到奧登序言的打字稿後不久,瑞典的外交官就登門拜訪奧登,暗示他瑞典學院不會樂見這樣的說法出版,最好加以修改。奧登不為所動。關於這個插曲奧登似乎僅提過一次,在當天他與友人Kirstein用餐時,說了這麼一句話:「諾貝爾獎就這樣吹了。」當年諾貝爾文學奬頒給沙特,不過他不領情拒絕了。
其實奧登一向很配合編輯的要求,但碰到他堅持的信念則不打任何折扣。
根據孟德爾頌教授的說法,奧登在無私地給予金錢、時間與愛心的同時,卻將自己外表塑造成不知變通或淡漠,可能源自於對成名太早的反動,奧登年紀輕輕就被視為英國左派文學英雄。
1939年他之離開英國前往美國,部分是為了逃開他這樣的公眾形象。他曾在一次政治集會做了一場演講後寫信給友人說:「我突然覺得我真的做得到,我可以來一場極具煽動的演說,讓聽眾熱血沸騰。。。。很讓人興奮沒錯,不過太墮落了;興奮後我覺得滿身污垢。」
他從自己身上看到權力與殘酷對藝術家有特殊的誘惑,藝術家也擁有特殊手法遮掩他們的念頭。他觀察到自己被偶像化、被仰慕感到滿足,但實際上對政治與道德議題並無特別洞見,這樣的差距讓他覺得墮落。
奧登顯以文學關懷人間烟火,感慨時代,以文學淑世,詩與行合一。西班牙內戰爆發,他去當救護車司機,名作〈1937的西班牙〉誕生。如果奧登比較會長袖善舞,他今天會是以諾貝爾文學詩人名世;但他走到街上,在人間煉詩影,是個有公民關懷的大詩人。想像若在今天的地鐵看到奧登素樸獨立,樟樹一樣的鄰居臉孔,皺靜沈吟詩稿,願為一位囚犯函授文學,願為公益當司機,下地鐵時抽根烟,人潮擠湧裡擦過諾貝爾獎,點燃文學街燈,是公民社會裡可愛的一景。
照片取自網路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